陈新月:总想为患者争取一个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2023-03-03 17:27

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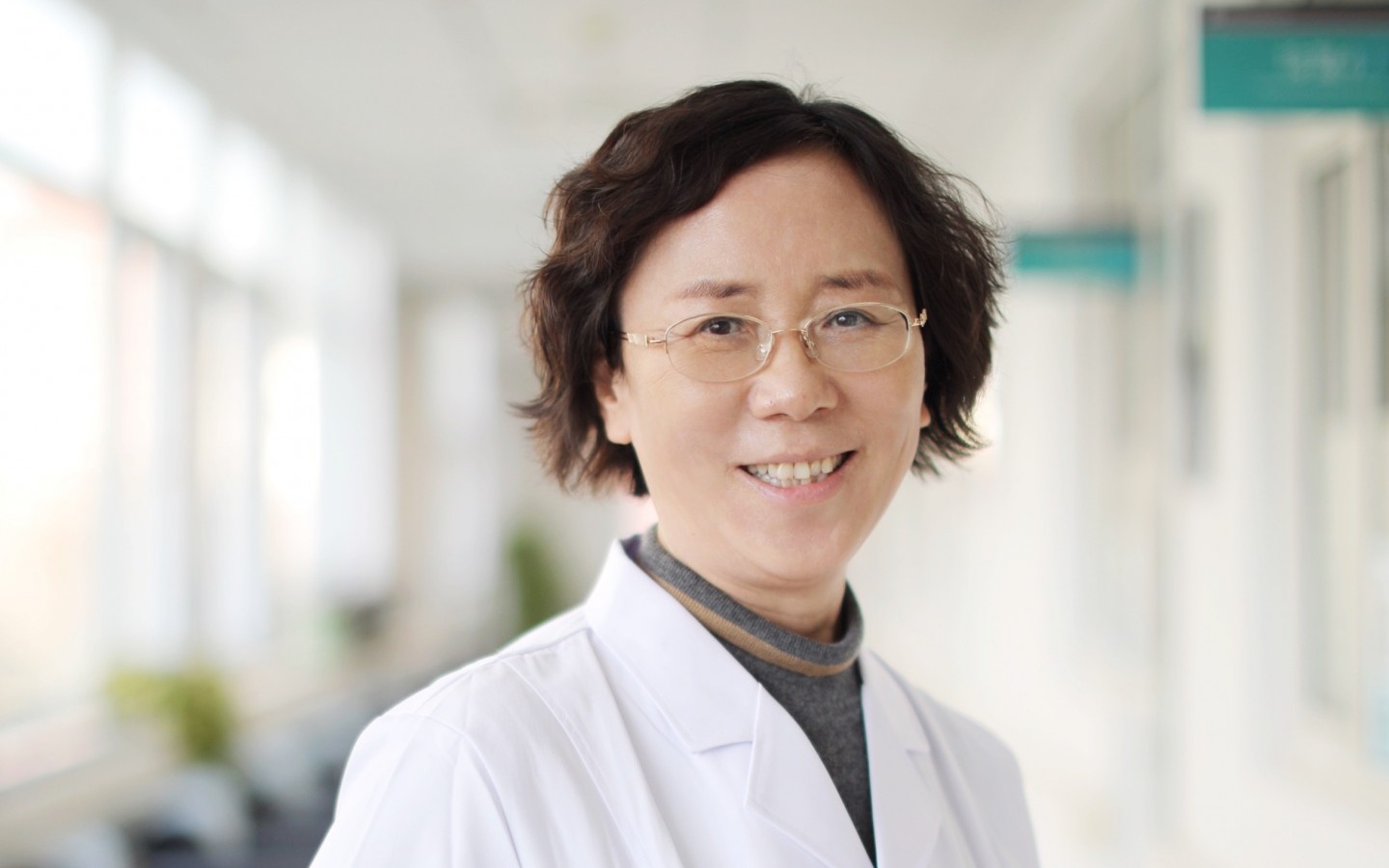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首席肝病专家陈新月。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名医简介】
陈新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首席肝病专家,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第五届—第七届全国委员,研究方向为慢性肝炎抗病毒治疗临床及机制,尤其对慢性乙型肝炎个体化治疗具有丰富经验。陈新月先后承担多项国家及北京市重点课题研究,曾获得中华医学会科技进步奖及北京医学科技奖。截至目前,陈新月共发表百余篇论著,包括发表在Hepatology、CGH及Liver International等杂志。
陈新月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首席肝病专家。“不管什么病,医生一治就好”是她当医生的最初想法;成为医生后,她是那个经常打破常规的人;从医四十年来,她觉得自己有点“倔”,不服输,总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她说,每一个疗效理想的案例背后,都是医生和患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从心里感谢患者”。
“医生一治就好”成为当初学医动力
陈新月的父母都从事教育工作,父亲有两位世交,都是医生,一位是牙医,一位是内科医生。陈新月小时候,父亲牙口不好,跟这位做牙医的朋友往来自然密切。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陈新月觉得医生是一个神奇的职业,“牙痛能治好,肚子疼和发烧也是,医生一治就好。”将来做医生的想法也在那时候开始,慢慢在陈新月心中萌芽。
中学毕业后,陈新月跟很多同学一样到农村插队。因为上学的时候跳过级,她看着比周围同学都小一些,可这不妨碍她对插队期间村民们遭受的疾病痛苦感同身受。
1977年,全国高考正式恢复,陈新月成为570多万考生中的一员。她觉得,能上大学就已经很好,专业是其次才考虑的问题。不过,小时候的医生理想和插队期间的感受都让十几岁的陈新月记忆犹新,她想学医,父亲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这样,陈新月考入南京医科大学。
进入大学后,陈新月遇到至今都感恩的老师——教感染学的陈仲英教授及贾辅忠教授,他们在江苏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那时候,“不像如今的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成为主流”,感染性疾病中细菌性疾病及病毒性疾病更为常见,疾病的受众也较广。当时内科常见的疑难问题例如:黄疸鉴别诊断、发热待查及抗生素使用等在老师那里均能迎刃而解。
陈新月坦言,“那会儿在专业的选择上,考虑更多的是兴趣,还没有到‘解除大多数人的疾苦’那么高的境界。”她的想法很简单,只觉得跟着自己的老师,能立竿见影地减轻患者的痛苦就挺好。为此,毕业后她就坚定地从事感染性疾病的诊疗,并跟乙肝结下不解之缘。
如果不是工作几年后,爱人考研到北京继续深造,陈新月可能会一直在江苏继续工作。不过,现实还是“推”了她一把。
陈新月本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江苏某医院工作。几年后,她的爱人考取了研究生,到北京读书,原本打算毕业之后,爱人继续回江苏工作,但因为各种原因,最终留在了北京佑安医院。
要一家人团聚,摆在陈新月面前的选择有两个:要么找机会调入北京工作,要么自己考到北京。有点“倔”的她选择了后者,“要来我就自己考过来,本科学历在地方医院或许还可以,要在佑安医院,我觉得还不够,我不是一个服输的人。况且我不想以一种类似’附庸品’的身份过来,我接受不了。”就这样,在本科毕业近十年后,陈新月走上了考研之路。
这一次,又是老师的影响,让陈新月觉得,自己选择的领域越来越有意思,越来越值得钻研。考研成功后,她成为林秀玉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毕业之后,全国著名肝病专家汪俊韬教授又给陈新月的从医之路留下重要影响。彼时,汪俊韬教授是陈新月爱人的导师,在佑安医院成立之初,留苏回国在协和医院工作的汪俊韬教授,曾作为专家来帮助和指导佑安医院科室建设。在佑安医院国际医疗部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陈新月作为科主任,汪俊韬教授作为特聘专家。陈新月说:“在抗病毒治疗中,如果我说一开始就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那跟汪俊韬教授的指点有很大的关系。”
治好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的幸福
“我骨子里是个要强的人,凡事都争取做到最好。”陈新月这样评价自己。在诊疗工作中,她确实做到了。
陈新月工作之初,公众对乙肝还有一定的认知误区,也不乏歧视眼光。常年跟肝炎患者打交道的陈新月,对这种感觉并不陌生。很多从外地来的患者,之前就诊时一旦发现乙肝病毒检测阳性,会被一些机构拒绝,或者一些检查只能在固定的地方做。但在佑安医院,患者没有这种“特殊”对待,“我不一定能给你治好,但最起码可以让你病情稳定、不恶化,为进一步治疗创造基础,从而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陈新月能深切地感觉到患者对疾病治愈的渴望与期待。如患者是初次就诊,陈新月会就乙肝病原学,致病原因,以及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和持久性等诊疗中的重要问题跟病人仔细介绍、沟通,让患者对自己的疾病有正确的认知。经过陈新月诊治后的很多患者就诊完后都有相似的感慨:“原来这个病没有那么可怕”、“大夫就像面对正常人一样跟我交谈”、“跟随陈主任就有可能得到治愈。”
王琴(化名)是一位乙肝患者,来自山东,她的母亲也是乙肝病毒感染者。17年前,还在上初中的王琴就已经出现对抗病毒药物耐药现象,这在当时是乙肝临床治疗中颇为棘手的问题。她慕名来到陈新月这里治疗,经过三年的持久治疗,王琴获得乙肝临床治愈。出于对未来治疗的考虑,高考时,王琴和全家人都坚定要报考北京的学校,就是希望离陈医生近一点。
现在,王琴已经博士毕业,前几天刚刚顺利生下一个六斤八两的宝宝。王琴的母亲也发消息向陈新月报喜,“特别有幸遇到你,她能跟正常的女孩子一样,可以没有负担地结婚、成为母亲。”王琴曾一度把结婚、生子视作奢侈品。
作为母亲的陈新月,对王琴妈妈的感受格外共情,她觉得,治好一个孩子,就是一家人的幸福,她为患者争取到一个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陈新月的骨子里带着一股认真劲。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致力于解决指南和规范之外的问题
在很多疾病的诊疗中,都有相应的指南和规范,这对医生的诊疗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陈新月并不满足于此,她是那个经常打破常规的人,她不满意自己在临床中抗病毒疗效仅限于对乙肝病毒的抑制以及e抗原血清学的转换。陈新月想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治愈更多的乙肝病人。为此,她在乙肝临床治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在缓解率百分比背后,治疗方案的设计是怎样的,把目光瞄准百分比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
举个例子,长效干扰素是治疗乙肝的一线用药之一,临床中通常用药的疗程为48周。但仅48周的固定疗程是否足够?不同的患者均相同的疗程是否合理?临床治愈率不高的原因何在?如何提高疗效?这些问题经常困扰着陈新月。避免把所有患者如同“大锅粥”般对待,就是陈新月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做的事情,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把患者中的基本人群、优势人群区分开来。有相当一部分患者,通过联合治疗、延长疗程后可以获得很好的疗效。她提出,临床抗病毒治疗中要做到定目标,不定疗程,延长疗程中也要兼顾安全、有效的原则。“只定疗程,有些患者未必能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陈新月希望的,是能够在标准之上,做到个体化治疗。
陈新月解决的问题远不止这些。非活动性的表面抗原携带状态的人群,即通常说的“小三阳”、乙肝病毒处于低水平、肝功能正常(免疫控制期)的人群,之前国内外标准都认为,无需治疗。欧美人群的数据显示,患者随访10年甚至20年后,有15%-45%的患者表面抗原自动转阴。继续随访的数据显示,这类人群发生肝硬化、肝癌的比例,与普通人群相比,没有明显差异。而来自台湾地区的数据表明:同类患者随访13年,肝癌的发生比例高出正常人群4.6倍,死亡率高了2.1倍,肝癌发生率是欧美相应人群的10倍左右。陈新月对不同文献的理解认为,中国人与欧美人群具有显著不同的疾病背景,如感染途径、病毒基因型等。
做事认真的陈新月,再一次“挑战”规范和指南,开始对非活动性表面抗原携带患者进行前瞻性、对照治疗。2017年,陈新月和团队的研究成果显示,非活动性的表面抗原携带患者不仅需要治疗,而且可以获得较高治愈率。通过联合、延迟治疗,有44.7%的患者实现表面抗原转阴或伴有保护性的抗体出现。彼时,这一结果在国内外的同行中引起关注,近几年来,更多的亚太地区人群治疗结果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部分医院通过筛选适合的患者,乙肝表面抗原转阴率已经可以突破80%。事实证明,陈新月和同事提出的方法,是行之有效,并且可重复的。随后,对11篇文献综合数据分析表明,非活动性的表面抗原携带人群,基于干扰素为基础的治疗,转阴率可以达到47%。完全支持陈新月的观点:非活动性的表面抗原携带患者需治、能治、具有较高治愈率。而且获得乙肝临床治愈者,大大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率,长期预后慢性改善。
“好多时候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儿”
治疗中往往还藏着她的一些“小心思”。以干扰素的使用为例,国际诊疗指南和规范推荐的注射剂量,通常基于标准人群(相当部分为欧美人群)的情况。“我们患者的体重,普遍会比他们低一些,如果按照指南的剂量来,一些患者可能就耐受不了了。”陈新月的做法是,适当降低注射量,延长疗程,用疗程补疗效。这可能是很多同行经常问陈新月“我们的(患者)怎么不良反应这么大、坚持不了长流程,表面抗原很低就是就不转阴?”的答案所在。
陈新月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自己的性格,凡事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尤其是临床上相对空白的领域,她愿意花费心思给自己也给同行探究出一条路来:“哪些患者是最适合延长疗程的,对哪些患者疗效不显著,可以暂停干扰素避免浪费,对哪些患者有效果,但不良反应又比较重,该如何避免(不良反应)并兼顾疗效。”围绕这些问题,陈新月和他的团队,在没有先例可以学习的情况下,一直摸索着。她说自己做事比较认真,骨子里带着一股认真劲,“好多时候都是自己在跟自己较劲儿。”
“这么多治疗转阴情况和成功的案例,都离不开患者的配合。” 陈新月从心里感谢患者,也在追求最佳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之间,寻求着平衡。
现在,作为佑安医院首席肝病专家,陈新月还在兼顾临床与科研,去年,她还和同行们发起“乙肝临床治愈星光计划”,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获得临床治愈。她开玩笑说,可能不久之后,同行们就吃不上“肝”饭了,因为在低年龄段,我们的乙肝防控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当。不过,现在还有相当数量的“库存”人群,尤其是在大年龄人群中,正处在疾病进展高峰,肝硬化、肝癌发病状况不容乐观。她觉得,脂肪肝、酒精肝、代谢综合征肝病,可能会是同行们以后要面对的重点。
吃了三十多年“肝”饭的陈新月,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吃饭状态。因为长年门诊量超负荷、必须久坐,她经常感到腰酸背疼,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再年轻,现在的陈新月也在试着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出门诊时,前后两位患者就诊的间隙,她都会站起来活动活动;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她现在都站着吃饭。按摩也成为她工作之余喜欢的事,原因很简单,能缓解疼痛。医生的身体也未必那么好,但她觉得,自己又必须得是个“铁人”。
年轻时,陈新月喜欢看小说、看电视、旅游,慢慢地,这些爱好已经被工作“挤”得几乎没有时间做了。以前,在医院忙完一天回到家,实在太累,她就先吃晚饭,10点钟左右睡一会,11点左右起来,继续忙工作到一两点钟。她用“倒下就能睡,起来就能干”来形容那时自己的状态。现在,睡眠质量不如从前,陈新月不敢再这么熬,12点左右就已经入睡了。以前,她的床头总会放一本小说,睡前翻一翻。现在,为帮助入睡,她会打开手机APP,听一些感兴趣的节目,调低声音,调至0.75倍速,通常听半个或一个小时,她就能睡着。
陈新月还是希望能尽量留出一些时间,给自己和家里人,趁周末到郊区走走看看,住民宿、吃农家饭、打扑克牌,是最能让自己轻松的方式。
新京报记者 张秀兰
校对 柳宝庆
来阅读我的更多文章吧
张秀兰
新京报记者
记者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