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诗语言优美,情感丰盈,意象新鲜,但有时晦涩难解。从阅读角度看,“晦涩”是现代诗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然而,这晦涩无论是源于特定的表现方式,抑或对诗之新奇的追求,还是对“何以为诗”的定位,一首好诗不可能仅表现在晦涩,而必须值得深入阅读,让读者在认知与想象的主动参与中,发现晦涩中那复杂的诗意,充裕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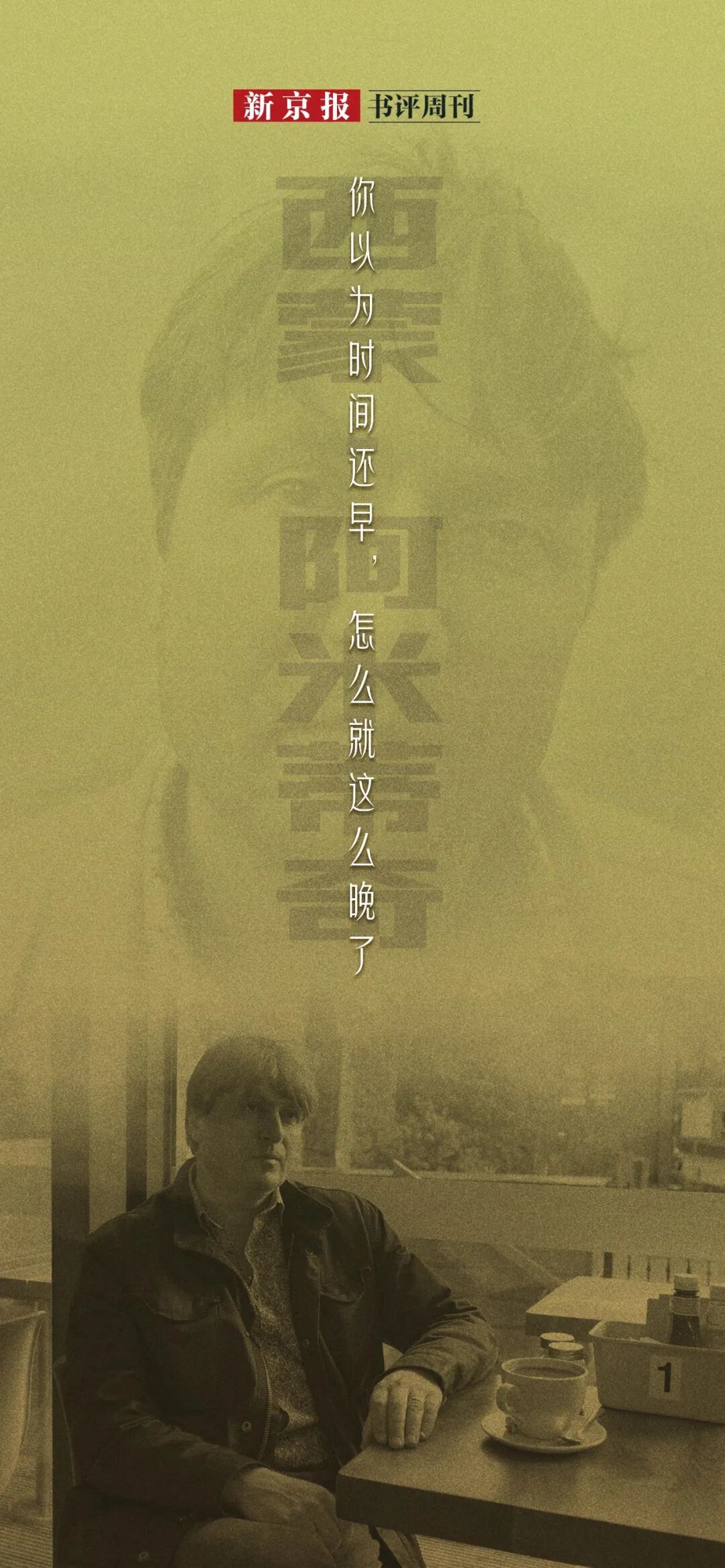
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1963-),英国当代诗人,作家。2015年获授牛津诗歌教授一席。
本期诗歌
傍晚
作者:西蒙·阿米蒂奇
译者:李晖
你十二岁。顶多十三岁。
你正从后门走出这所房子。
时间还不晚。你答应过
不去太久,也不走太远。
有一天你会晓得这些树的名字。
你走上山脚下左边的岔路,
沿两条小溪间那条马道。
这里是沃尔峡谷。这里是罗伊德悬崖。
山峰仍然有太阳照着。但已是
傍晚。傍晚赶在你前面上了山坡。
暮色自你脊椎的关节往上移动它的手指。
你突然转过身。回到家
你的孩子在床上熟睡,那床已经有些小了。
你的妻子在灯光下缝补衣物。
你难过起来。你以为
时间还早,怎么就这么晚了?
诗歌细读
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英国当代诗人、作家,1963年生于马斯登镇,在西约克郡长大,毕业于朴次茅斯大学地理专业,随后取得曼彻斯特大学的硕士学位。2000年,他因出版千行诗《消磨时光》而成为英国的“千禧年诗人”;2015年,他击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索因卡等强有力对手,当选牛津大学第45任诗歌教授;2019年,西蒙·阿米蒂奇被首相特雷莎·梅任命为英国桂冠诗人。他获过很多知名的诗歌奖,但我好奇的是他读大学时曾经学习的专业——地理学。
西蒙·阿米蒂奇写过一本纪实书籍《流浪到故乡》,记述他的一次翻山越岭徒步的经历。2010年7月7日至26日,他身上没带一分钱,靠沿路为居民朗诵诗歌来换取旅费,由北向南穿越奔宁山脉回到家乡,全程走了大约400公里。有着地理专业的背景,他对山川大地的兴趣不仅仅止于徒步奔波,他对时间概念的兴趣同样也与地理分不开,毕竟时间是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这首《傍晚》虽然只有短短十六行,但却几乎跨越了一个人的一生。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推开门走出去,“不去太久,也不走太远”,一路行走,也并没有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情,但当他回到家后的景象却叫人倍感惊悚。这是一首描写时间的诗,此类诗词古已有之,从庄子“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韦庄“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到苏轼“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朱熹“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等,无不感叹时间如梦如电,转瞬即逝。但若论和西蒙·阿米蒂奇这首诗的相似度,莫过于李白在《将进酒》中的一句诗: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不知道阿米蒂奇是否读过李白这首诗的英译,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个相隔千年的诗人,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生如一日、转瞬即白头的感觉体验。和李白的《将进酒》不同,李白是登高饮宴,借酒放歌,感叹人生易老,抒发自己的愤激情绪,阿米蒂奇则从极为具体的生活细节着手,将读者一步步带入他的所观所思:一个孩子从后门离开家,答应家人不会走太远,去去就回。注意,“从后门走出”也许埋下了一条理解这首诗的线索,但只有读到最后一段才能明白作者的用心。接着,诗人开始展示他地理生的眼光,引导读者去“看到”这个孩子经历的景象:山林间的树木,山脚下朝左拐的那条岔路,位于山谷中两条小溪之间的一条马道,孩子到了沃尔峡谷,又登上罗伊德悬崖。
按照一般的理解,一个孩子如果花半天时间大约是能够走这么远的路程的,但显然并不符合他“不走太远”的承诺。作者的高明在于,他的笔墨一直都在描述山间地理的变化,这条线路牵引着读者的视线和注意力,让人完全忽略了时间问题。到了第三段,作者终于“漫不经心”地写到了时间:
山峰仍然有太阳照着。但已是傍晚。傍晚赶在你前面上了山坡。 暮色自你脊椎的关节往上移动它的手指。
一天将尽,黄昏来临。时间开始超过主人公的脚步,走上了山坡。一阵寒意随之袭来,“暮色”这时间的手指在他的脊柱骨上一节一节向上移动,提醒他黑夜即将到来。就在这时,这个孩子“突然转过身。回到家”。他看到了什么?——他的孩子睡着了,妻子在灯下缝补衣服。这突兀的一幕,不禁令人惊惧。时间就是这样流逝的吗?当读者还停留在那个十二岁孩子的背影上,却不知已物是人非、“朝如青丝暮成雪”;从“后门走出”并没有踏上时间线性的道路,而是超越现实地乘上了一条加速度的时间飞车。

约翰·康斯特布尔《威茅斯湾》,1816。
记得有位思想家曾说:人类所有的悲伤都来自时间。时间带走我们的所爱,带走幸福的瞬间,带走我们想挽留的一切,最终我们自身也被时间带走。但时间到底是什么?诗人感受里的时间和钟表标志的时间是一回事吗?
199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国家技术标准协会开始使用著名的NISTF-1原子钟,它是目前世界上最精确的时钟,用来定义宇宙时间坐标。但即便是如此精确的原子钟,也被科学家认为每2000万年会“遗漏”一秒钟。关于时间,古今中外不计其数的著名物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发明了许多概念,“纯粹时间”“相对时间”“不同步的宇宙”“有时态与无时态的时间”“广义相对论与时间旅行”“时间分支”“时间终点”等,每一种概念和学说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古代哲学家圣·奥古斯丁说:“什么是时间?如果没人问我,我是知道的。但当我试图向人解释时,坦白说,我一无所知。”
有意思的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诗人与哲人们对时间的描述跟物理时间迥然不同。尤其是诗人,在他们的感受和诗行里,似乎不存在可以用钟表计量的物理时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兮”,“度日如年心似煎”,“长夜漫漫何时旦?”,“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等等,时间时而漫长无涯,时而倏忽即逝。固有一死的生命,往往在跳出日常生活流的时候,才会突然发觉青山在、人已老矣!勿怪阿米蒂奇也为时光飞逝而叹息:“你以为/时间还早,怎么就这么晚了?”
这声叹息里有对生命衰败的惶恐,有对时光无法停留的惋惜,也有对时间本身的困惑。但是,如果他知道物理学家朱利安·巴伯的观点,会不会有些许安慰?——巴伯认为,时间在理论上业已终结,“时间是一个比人的想象力更为匮乏的实体,比如它不具有时态、违反牛顿原理、非线性,甚至不成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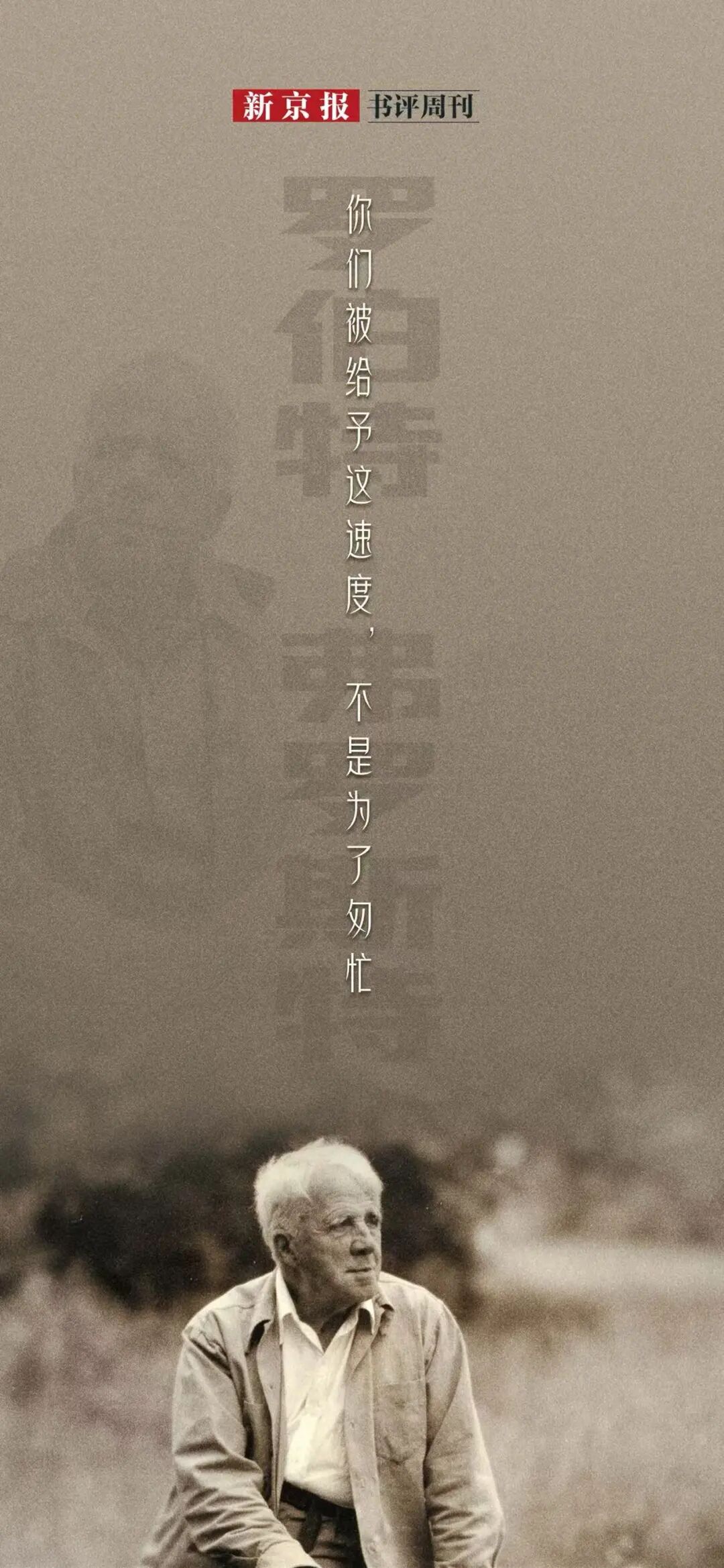
作者 / 蓝蓝
编辑 / 张进 李阳
校对 /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