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美国教授曾经好奇地问笔者,对赤脚医生有什么看法。笔者答复,自己从未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过赤脚医生,也并未从父母辈那里听过有关赤脚医生的描述。笔者对赤脚医生的了解实际上全部来自在西方出版的学术著作,而非自身在中国的日常生活。教授对此感到惊讶。其中隐藏的悖论是,西方学界对赤脚医生的浓厚兴趣甚至于将其浪漫化的叙述,和当代中国青年人对于赤脚医生的陌生感。方小平教授在《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以下简称《赤脚医生》)的自序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感受。
这本书实际上就发端于对这一悖论的反思。学界通常将赤脚医生的形象描述为“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强调赤脚医生在医疗实践中将中医和西医相结合的特点。现有研究大多认为,赤脚医生为中医药在中国基层农村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刻影响了中国如今中西医相结合的特殊的基层医疗体制结构。在赤脚医生的努力下,不同于其他国家本土医药日渐式微的生存危机,中医获得了和西医相对平等的专业地位。但这些对赤脚医生浪漫化的描述,显然与生活在中国基层的人们的日常医疗生活经验相差甚大。
方小平写道,他出生于赤脚医生发展的巅峰时期,却鲜有服用中草药治病的童年记忆。中药于赤脚医生的意义和中药在中国基层的发展是否被学界夸大?在方小平看来,对于赤脚医生的讨论,更应该着重于西医,而不是中医。赤脚医生是将西医带入中国乡村的载体。更关键的问题是,赤脚医生如何将西医药带入曾被中医药主宰的中国乡村医疗世界,进而实现了中国乡村卫生系统的转型?
方小平以杭州市余杭县蒋村乡作为研究案例,收集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相关地方档案,并对村民和医生进行访谈,来呈现赤脚医生项目的历史发展及其对中国乡村卫生系统的影响。方小平认为,“文革”时期的赤脚医生项目(1968-1983)实际上是西医在中国农村取代中医主导地位的关键历史转折点。国家、医生和村民都是这一乡村卫生系统转变的重要行动者。赤脚医生通过专业化进程,向中国乡村推广西医药。而国家是赤脚医生专业化进程的关键支持者。西医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化,建立起新的乡村医疗制度。村民被纳入国家医疗体制的对象,其医疗消费习惯转变为偏好西医。中医在这一过程中被边缘化。
《赤脚医生》一书突破了许多现有关于赤脚医生的认知误区,例如西医而非中医在赤脚医生项目中占据优势,且很好地呈现了国家、医生和村民三者的互动。但此书把很多对蒋村赤脚医生项目的讨论泛化到中国乡村医疗世界,一则夸大了蒋村案例的代表性,二则忽视了民间医疗市场的存在与中医的影响力,误将赤脚医生项目在国家乡村卫生系统的实践泛化为乡村医疗卫生的全部实践,三是忽视了民国时期医疗发展的影响。此书聚焦于赤脚医生的职业发展,但也因为这一焦点而模糊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有过分强调赤脚医生影响并泛化到乡村医疗世界之嫌。但笔者依旧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优秀著作,并尝试将此书的理论贡献拓宽到职业社会学领域中。
撰文|吴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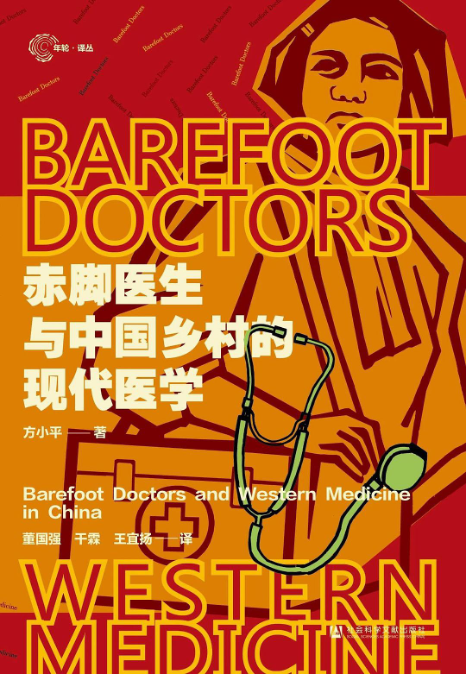
《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
作者: 方小平
译者: 董国强 / 干霖 / 王宜扬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年4月
乡村医疗的历史发展
关于中国乡村医疗的发展历史,在一般的历史叙事中,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1929年余岩“废止中医案”为标志,中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而在1949年后,中医的合法性得到了国家的承认。中医获得了行政权力,被纳入国家医疗卫生体系,进而得以迅猛发展。方小平批评这一历史叙事误读了中国乡村医疗世界的中西医格局。他认为,实际上,中医在乡村医疗世界的主导地位并未在民国时期被撼动,而至少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医在乡村影响力的衰退是发生于“文革”时期的赤脚医生项目。此后,西医,而非中医,占据了乡村医疗的主导地位。但方小平的历史叙事也有几点值得推敲之处。
首先,中医是否不再占据乡村医疗的主导地位?读者们其实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就会发现,中医在乡村世界乃至城市仍有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反观方小平的叙事,实际上国家的支持,而非消费者,是他衡量中西医在乡村医疗地位变化的关键变量。对其历史叙事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西医在国家乡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地位于“文革”后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国家卫生医疗体系随着赤脚医生项目在中国乡村扩大了影响力。如方小平在第二章的论述中所提到的,赤脚医生内部实则也认可中医的合法性,但西医的增长远大于中医。因此,国家借赤脚医生项目在农村发展的基层卫生体系是更偏向于西医。但是,医疗市场内部国家医疗与民间医疗、中医与西医并非零和博弈。通俗地来说,病人会前往公立医院就诊的同时,也可以前往民间传统医疗场所寻药。因此,方小平捕捉到的西医于国家基层卫生制度的迅速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医于民间医疗市场的衰退。
其次,乡村医疗中西医格局转变的关键历史转折点(turning point)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项目,还是民国时期的废除中医运动?方小平认为,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中医的限制并未深刻地影响到乡村医疗世界,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国家承认中医的合法性,但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要求中医也应学习西医,例如中医的执业资格考试也包含西医的专业知识,中医实际上成了西医知识的传播代理人,西医借以赤脚医生项目在乡村医疗世界的迅速扩张。这一叙事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府在基层医疗资源动员能力上的差异,二是西医与中医职业竞争的转折究竟发生在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笔者认同新中国成立政府在乡村的动员能力大幅提高,因而西医可以借助国家力量于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医对西医的学习,或者说同构(isomorphism),于民国时期就已存在。赤脚医生项目的主要贡献是将乡村医疗纳入了国家医疗体系,即在基层医疗体系中加深了西医与国家的合作,但如上所述,《赤脚医生》并未能给出更多关于民间医疗市场里中医的发展概况的经验数据,来论证中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纪录片《赤脚医生》(1975)剧照。
蒋村赤脚医生能否代表乡村医疗?
这便涉及《赤脚医生》的研究方法的代表性问题。第一,方小平所收集的访谈资料包括近50 位原赤脚医生、当地群众和基层干部,并未涉及民间医疗实践者,比如中医和巫医。这导致这本书实则是关于赤脚医生乡村发展史,而非中国乡村医疗发展史。这本书很好地描述了在蒋村的赤脚医生、国家和村民在“文革”时期的互动以及对政府基层医疗体系发展的影响。在一部讨论某一职业发展(本书即赤脚医生)的著作中,作者能不将视野局限在该职业本身,而能够把消费者、国家以及竞争者很好地纳入讨论,是难能可贵的。但笔者并不认为,《赤脚医生》的研究结论可以泛化到代表整个乡村医疗世界,因为其缺乏对竞争者(民间医疗)的充分讨论。
第二,基于杭州蒋村田野数据的《赤脚医生》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以代表中国乡村医疗?方小平认为,“赤脚医生运动是一项高度同质化的全国运动”。即便赤脚医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同质化(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乡村医疗在“文革”之前全国范围内是高度多样的,因此即便赤脚医生项目的政策规划是同质化的,其结果必然是不同的。可以想象,位于省会的蒋村拥有比很多乡村更优越的西医资源,西医在赤脚医生项目中发展会比其他地区顺利许多,这使得蒋村实际上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笔者在此想提醒读者的是,在阅读过程中谨记这是一本关于杭州蒋村赤脚医生职业发展的优秀著作,需要仔细斟酌其结论是否可以代表全国乡村医疗世界的发展。

纪录片《赤脚医生》(1975)剧照。
赤脚医生的职业发展
如果将《赤脚医生》定位在一本关于蒋村赤脚医生的职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professions)著作,这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一般认为,职业(professions)不同于一般的蓝领工作,利用其宣称的专业知识效用,宣告并获得某一特定领域管辖权(jurisdiction)和自主权(autonomy)。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ott) 从职业间关系视角出发,在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中聚焦职业如何利用其自身的专业知识,诊断出某类问题,并宣称可以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借此建立起其他职业无法有效管理的工作内容边界,进而夺得在某一特定范围内的排他性的管辖权。阿伯特的贡献在于从知识的角度提供了对职业内部结构的理解,至今鲜有人超越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对职业社会学的影响,但这对学科发展而言并不一定是益事。职业系统并不是无人监管的自由市场,国家在阿伯特的理论中是缺位的,且有许多例子可以佐证知识的效用既不是职业获得管辖权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文革”时期的赤脚医生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将赤脚医生项目纳入职业社会学的考量,可以很好地扩展现有的对职业的理解,特别是关于什么是职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遗憾的是,方小平在书中更多将自己的贡献落脚于对赤脚医生和乡村医疗的新理解,把赤脚医生的职业发展作为乡村医疗发展的重要变量,而没有系统地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如何有助于我们产生对职业新的理解。方小平把《赤脚医生》的理论贡献放错了地方。在接下来的讨论里,笔者会借此书再诠释赤脚医生的职业发展,以挖掘本书对职业社会学的理论贡献和留待探讨的问题。
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西医如何借赤脚医生项目在与中医的竞争中赢得在国家乡村医疗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赤脚医生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其职业发展?
第一,赤脚医生的知识结构西医化。在职业教育层面,西医的教育门槛实际上是低于中医的。方小平的这一发现突破了对医学教育的常识性认知。由于赤脚医生的选拔标准主要看重家庭的政治面貌,不同于以往传统医学更加注重家庭内部的传承,赤脚医生来自普通农村家庭,而非之前那样来自乡村精英家庭。人们可以前往县级赤脚医生培训班,较为便利、快速地训练成为赤脚医生。这降低了医学教育的门槛,增加了乡村里医学知识者的数量。而与此同时,赤脚医生中少数的被吸纳的民间医疗者们,其培训模式仍然为保守的师徒传承模式,虽然对徒弟的选拔标准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弟”。这导致虽然赤脚医生群体也吸纳中医,但西医的增长远高于中医。中西医的数量增长并不均衡。在赤脚医生中,西医远多于中医。
但方小平在叙述中没有注意到的是,中西医本身的职业化程度是有显著差异的,这是导致赤脚医生内部西医数量远高于中医的重要原因。由于西医的职业化程度远高于中医,其专业知识和职业培养有一套系统化的职业标准,并且拥有大量的医院作为训练的场所,有中医所缺乏的制度支持。这些西医相较于中医的职业竞争优势是被方小平忽视的,而这背后,如上所述,是由于方小平对民国时期中国西医职业发展的忽视。
另外,赤脚医生准入门槛之低,实际上是非常有趣的职业现象,而遗憾的是,方小平未能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对此展开讨论。职业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其拥有的专业知识,且这一专业知识是他人难以获得的,是垄断性质的。而获得专业知识的训练过程和准入门槛,使得对职业的想象一般是精英化的形象。赤脚医生的存在打破了这一想象。赤脚医生是职业群体,却又并非精英群体。方小平提到,赤脚医生实际上是“穿鞋医生”,极少会赤脚进入农田从事农业劳动,而是凭借其治病救人的专业技能生存的。但赤脚医生的收入却不高,其工作定位是非营利性的。赤脚医生的职业属性和其社会阶层形成了反差。专业知识的垄断反而无助于其职业发展,例如中医知识的家族传承阻碍了其在赤脚医生项目中的发展。赤脚医生项目可以提供关于职业发展和知识训练关系的新的理解,即更专业、更复杂的知识是否一定会给职业发展带来更好的收益?

纪录片《赤脚医生》(1975)剧照。
第二,从职业的消费者角度出发,方小平提出,赤脚医生项目的发展,促使村民的医药消费偏向于西药,进一步使得中医在日常医疗实践中被边缘化。先前的研究认为,国家为了降低医疗成本,鼓励赤脚医生大量使用中草药,对赤脚医生的形象描绘停留在“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但方小平所收集的经验数据显示,中草药运动在杭州地区的总体情况并不理想。中医药并不像之前研究所想象的拥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其制作与获取十分复杂,对大部分受过系统西医训练而没有受过深刻中医训练的赤脚医生来说,中医药的可及性并不高。很少有西医在诊疗过程中使用传统的中医技术,而中医都会同时使用中药和西药来诊断和治疗。并且,西药在防治传染病上具有优势。这使得村民的医药消费更加偏向于西药。
这一段叙述的问题在于,主要行动者的指代是模糊和不准确的。方小平将赤脚医生的消费群体泛化为所有村民,进而使其结论中西医药在赤脚医生项目中的优势过度引申到全体乡村医疗。赤脚医生项目里西药获得的相较于中药的优势地位,并不意味着中药在民间医疗失去市场优势。西药固然在传染病防治上具有优势,但中药对疾病的救治效用也不容忽视,且有着文化上的优势,在乡村有很强的文化亲和力,这也是至今中医药仍能占有广大市场的原因之一。

纪录片《赤脚医生》(2016)剧照。
此外,赤脚医生作为专业群体,如何定义并理解其专业身份,在书中是缺乏讨论的。笔者认为这其实可以是赤脚医生案例最有趣的理论贡献点所在,即为职业社会学提供关于什么是职业的新理解。笔者认同方小平将赤脚医生理解为特殊的职业群体,拥有独特的专业知识和工作领域。但赤脚医生的专业知识的特殊性在哪里?与一般的中医、西医有什么不同?如何理解和定义赤脚医生群体中的中医与西医?其专业知识的特殊性如何影响了其具体的工作实践,并造成赤脚医生项目的西医优势结构?这些问题在书中没有明确的答复,却是理解赤脚医生专业身份的关键所在。笔者期待能有更多关于赤脚医生的研究,来扩宽现有研究对职业的定义。
第三,国家在赤脚医生专业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作用。赤脚医生是政治权力影响职业发展的典型案例,而专业系统之外的权力关系是在阿伯特的理论中被忽视的。方小平遗憾地未能就此进行理论对话,笔者希望借以下讨论来扩宽《赤脚医生》的理论贡献。
国家在组织制度、职业竞争与群体认同等方面支持了赤脚医生的专业化发展。首先,国家于1968年建立了由赤脚医生主持的村级医疗站,同时赤脚医生可以转诊病人前往县级以上的医院就诊,赤脚医生和县级以及以上的医院的重要性急剧增加,而居于中间层级的公社卫生委急剧衰退,形成了两头宽中间窄的哑铃形结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通过将村民纳入国家医疗体制对象,使赤脚医生拥有广泛的消费群体。群体身份认同层面,国家通过赋予“赤脚医生” 强烈的革命色彩,来给予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赤脚医生的非营利性,减少了其职业内部的竞争,并且由于其鲜有晋升机会,使得这一群体在1960-70年代具有稳定性。而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反迷信”运动,边缘化了其他的医疗竞争者,为赤脚医生的群体发展提供了支持。
以上可以看到,职业群体如何通过国家的动员能力来确立自身的职业地位。赤脚医生与国家的深度捆绑,使其成也国家,败也国家。1985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全国卫生局局长会议的闭幕式上宣布卫生部决定不再使用(“文革”中)沿袭下来的、含义不确切的(赤脚医生)名称,于2 0 0 9年各县开始培训农村社区医生来填补大规模退休的农村社区医生(曾经的赤脚医生),方小平预言,“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赤脚医生群体在不久的将来会从中国乡村医疗世界中彻底消失。
这便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问题。对许多当代青年人而言,赤脚医生是日常生活中陌生的存在,却又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方小平所批评的对赤脚医生浪漫化的叙事,实则是存在于现代学术知识中的东方主义话语(Orientalist Discourse)。在对此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更要问的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讨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对当下世界的意义何在?仅将其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也是一种东方学的再现——把东方的历史视为特殊的存在。笔者期待,能有更多的优秀研究借赤脚医生挖掘出对职业、医疗、权力更普遍的理解。当下此起彼伏的诸多新闻事件,常被戏谑是离谱的闹剧。但历史早已一遍遍地提醒我们权力的存在。笔者在此并非想强调福柯式弥散的权力监管,而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优秀研究不止步于仅仅讲述中国案例的特殊性,而是站在中国案例的经验之上与主流学术进行真正的对话。
撰文/吴琼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