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季、秋招季即将开启。新生开始踏上专业学习之旅;准毕业生(从本科生到硕博士研究生)则通过投递简历向招聘者介绍所修专业。
什么是专业,或者说一门学科是什么?这是今年6月20日,我们在第一期“我和我的学科”专题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每一门学科都提供了帮助人求职生活的专业知识、技能,也可以说每一门学科其实都是在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现在,我们再续“我和我的学科”的故事,请新闻传播学、法学、流体力学、昆虫学等传统基础学科,以及机器人工程等新兴交叉学科的高校教师,以第一人称讲述。既谈这个学科是什么,也谈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与学科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他们在教学中产生的对于本学科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本篇为赵宏谈法学。
今年六月我和几个法学同事一起做一个公共讲座,到了提问环节,一个观众起身问道,孩子即将报高考志愿,他很希望孩子能学习法律,就想问问台上的几位老师,究竟具备什么样的素养最适合学法学。如果是在更年轻时,拿起话筒的那刻我大概会侃侃而谈,那当然首先得逻辑好,思辨性强,因为逻辑思维和思辨能力大概是法律人最常自矜的素养。影视剧在刻画法律工作者时,能言善辩似乎也总是定番标配。
但在法学的世界里浸淫了这么久,我的答案已经有了全然变化,如果现在再说什么对法学学习更重要,我会坚定地选择同理心和理想主义。同理心是因为法律说到底关心的是具体个人的权利和处境,如果无法在抽象诫命下看到个体命运的起伏,法律充其量就只能被称为“技艺”,它会变为最冰冷无情的治理机器,也会将所有的不法都掩盖在法的形式之下。而理想主义又是因为,或许唯有真的怀抱朴素的法治理想才能让原本应服务于正义和良知的法不致被魔鬼和野心所驱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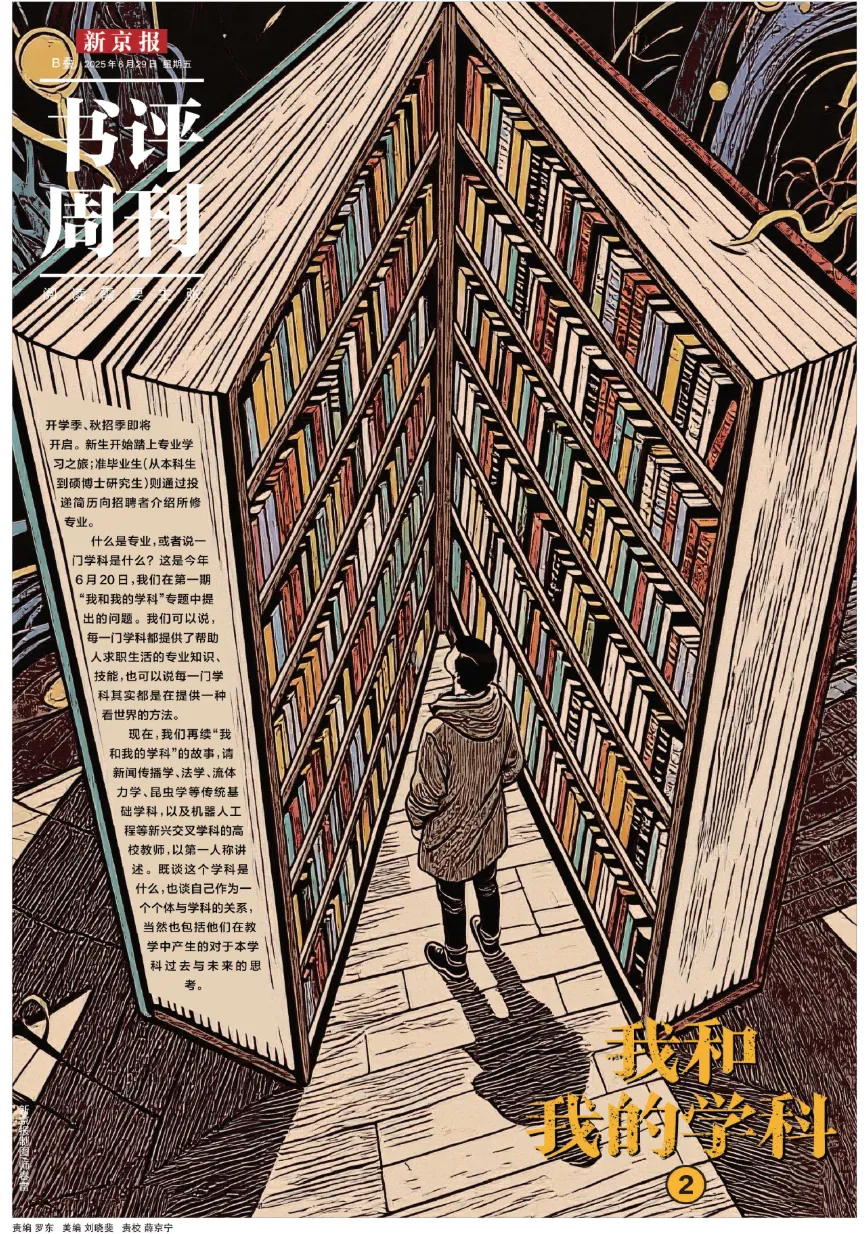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29日专题《我和我的学科》B04-05版。
撰文丨赵宏

赵宏,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公法、比较公法、国家学、个人信息权的公法保护等,长期关注和参与公众法治教育。
法律理想主义的火种
这是经过了20多年的答案。时间再拉回到我高考时,选择法学作为职业就真的纯属巧合。我们那个时代的高考还没有张雪峰指导志愿填报,所以横亘在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信息差也决定了每个考生的专业选择。我来自西北的一个中等城市,所谓中等,其规模也不过就是全市总共三所中学。因为中学阶段学业表现突出,高考之后的估分和志愿填报,我都是在各科老师的共同监督商议下完成的。在我之前,母校高考的最好成绩似乎只是兰州大学,我也当然成了学校能创造高考佳绩的重点培养对象。当时学校对我的要求首先是必须是北京的大学,其次必须是所重点大学,几经权衡班主任帮我定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还言之凿凿地跟我父母说,学完法学就可以进政府机关当公务员端铁饭碗。但不敢冒进的父母在最终提交志愿时,还是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偷偷改成了分数更低一点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反正学法学都要当官的,而且这俩学校名字里还都有“中国”,应该也错不到哪儿去。于是我就这样进了法律系,走上了法律之路。
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生部在昌平,所以我的大学四年都是在昌平度过的,现在看大学毕业照真的就是土得掉渣的“昌平Style”。但就是在那个狭小简陋的校园,我们却接受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法学教育。中国政法大学有个传统,但凡新生入校,都会集体宣誓“执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当数百人的声音回荡在大礼堂,那一刻也成了我关于法律最初也是最永恒的记忆。

电视剧《以法之名》剧照。
初学法律的几年,很多法律尚未制定完成,老师们授课时最擅长的都是批判法学,法条基本是不提的,法规也基本是不看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痛批现行法中存在的各种漏洞问题,而我们提交的报告论文也基本都是立法论性质的,每个人都要填补法治漏洞,每个人都有绘就法治蓝图的宏愿。这跟我们现在讲法律时会说,学会找法懂法解释法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领,法律人首先要尊重实定法的权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符合价值判断的解释,真的有天壤之别。
可也许就是这种批判法学的教育模式让那个时代的我们都很有批判精神。现在想想,那也真是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宿舍同学倾巢出动涌向大礼堂听江平校长讲座时的情形,他讲学法律的首先要懂得区分“法制”和“法治”,前者只是约束个人,而后者同时约束权力;他讲法律的终极使命是捍卫每个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他还讲中国私法的空间是公法给的,个人权利的多少取决于国家权力的界限。这些话对于初入大学的我们好像一团火点燃在心里,也种下了最初理想主义的种子。我大学毕业后选择读宪法与行政法学作为硕士和博士研究方向,也跟老校长当时的启发教诲有关。
追求理性、面向现实的梦幻学科
除了正义的理想外,对于倾向于追求秩序和热爱规则的人而言,法学同样是梦幻学科。因为它就是由概念、规则、逻辑和体系构成,也用逻辑和理性来界分善恶,明辨真理。而那些包裹在繁复法条背后的又是极致的图标对称和逻辑完美。我后来读硕士时开始学德语,博士时选择做德国公法,除了因为我专研的宪法和行政法学基本以德国法为范本外,同样因为德国法的精密构造和繁复肢体简直就像巴洛克建筑和音乐一样令人着迷,它把抽象性和逻辑性推向极致,沉溺于这些规则构造里带来的脑力激荡,就足以让人产生如康德所说的“教义微醺”。
除了这些抽象学理,这个学科又总会让人不断接触社会真实。我硕士时已从昌平校园搬到了海淀小月河畔。那时的研究生还没有大范围扩招,一个年级的研究生统共也没有多少人。宿舍楼也是男女生混住,男生占据了一层和二层,女生在三层。这个男女比例跟现在法学院几乎都以女生为主已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宿舍楼前有个宣传栏,上面写着一行话是,“人民送我学法律,我学法律为人民”。那并非简单的口号宣传,每次经过真的会内心激荡。因为学校门口总会有很多从全国各地跑来上访的群众,会向老师和学生寻求法律帮助。楼下的男同学中甚至还有将自己的床铺腾出来给上访群众借住的。可以说,我们最初的职业自豪也基本都是在给这些上访群众提供法律支援时获得的。

《权力的边界》
作者:赵宏
版本:果麦文化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3年11月
读书时发生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法律事件是孙志刚在收容审查期间被殴打致死案和唐福珍为抵抗强拆自焚案。当时很多法学老师都发表了群情激愤的意见,这些意见甚至最终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并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成为这些事件的亲历者,会真实地看到法治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沟壑和张力。但在那个时代,这种张力却不会让人虚无、软弱甚至犬儒,反而会激发出改变现实的精神力量。
现在想想,那些精神力量更多来自于我们身边充满正义感的老师的言传身教。所以我自己在当了老师后也常常会想,我们在法学院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我又该向学生传达什么。专业性当然是需要的,因为法学毕竟关系他人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但只有法学专业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纯粹技术性的法学可以为任何人服务,也可以被任何人利用,每个受到良好训练的法学家完全可以证明出权力所需要的任何结果,甚至可以逻辑自洽地将任何行为解释为犯罪,并使之受到惩罚。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培养的首先是好的公民。好的公民意味着不仅自己要有专业持守,还要对社会和他人负担起责任。
法律人的宿命和责任
从中国政法大学到北京大学,我教过的学生几乎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现在在入学时我总会先给他们泼盆凉水,进入顶尖大学的法学院学习,并非只是靠个人的天分和努力,家庭的付出、社会的托举都必不可少,将个人取得的成绩都仅归因于自身奋斗并不客观,相反,唯有你意识到自己现有的成绩可能只是来自命运的馈赠,才会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也会意识到自己对于那些并没有那么幸运,甚至人生遭遇厄运和跌入谷底的少数人的责任。所以,我在法学院里教书时也总会说,法学说到底关心的是每个具体的个人,所要做的就是护住每个人个体的尊严,不让它为外力所纠缠和贬损。这就是我们法律人的人生目标,也是我们日复一日为此努力工作的真正原因。

电影《辩护人》剧照。
但为少数人辩护也总会遭遇公私目光的质疑,这也可能就是法律工作者的宿命。就像讲座时总会有人问,如何看待公众的朴素道德与法律甚至司法判决之间的关系。大众意见或者朴素法感与立法或判决相去甚远的事情又每天都会发生,我们一方面要克服专业法律人的倨傲,当某个判决结果与公众法感之间出现严重悖离时,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执法、司法甚至是立法出现了问题,比如此前发生的陕西菜农售卖5斤超标芹菜就被罚款6.6万的案件;但有时当互联网出现一面倒的对某些个体的道德鞭挞和公开处刑时,我们又需要站出来为这些“有劣迹者”辩护,并且有勇气指出法律所保护的个体尊严同样包括违法犯罪者的尊严。总之,选择坚持自己的法律职业操守可能面临的是两面不讨喜,在狂热时得提醒他们保持冷静;在高歌猛进时让他们记住刹车,恪守权力的边界。这也许就是法律人的使命,是命运对我们的职业召唤。
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法律同行者
不得不说的是,当下距离我上大学时已有很多变化。罗永浩在最近的脱口秀里吐槽,在年轻人看来,中年人已经有了原罪,只要开口指点天下,讲人生哲理就会被认为是爹里爹气的“老登”。年轻人也已经不再相信理想主义那一套,因为取代此前改变世界的雄心和理想的早已是对未来的焦虑,所以进入大学哪怕是理想的顶尖大学,也无非就是高中生活的延续,在学校的每一天都要为未来的考公保研做准备,我甚至听说连在大学里谈恋爱的比率在近十年来都开始急剧下降。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考公保研上岸似乎才是未来生活的真正停靠和心灵锚点。
我能够理解年轻人的焦虑,也能够理解他们对于中年“老登”的嫌弃,一如在呼啸前行的列车上,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被甩下,又怎么可能把视线再投放到他人身上。可能在被巨大的焦虑感所笼罩的年轻人看来,所谓理想主义和同理心也只是我们这些中年人对已经获取的红利的掩饰。但每次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又总会想到我上宪法课时的一件趣事。课间休息时我去卫生间,就听到两个女生议论,赵老师讲宪法中的人的尊严讲得很让人感动,可这种课对我们未来就业又有什么用呢?我当时认真想了想回教室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给出过一个衡量人的尊严是否受到侵犯的标尺,就是个人是否被客体化和工具化,我们在宪法上讲到这个问题时会说,人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达成某个目的的政治手段和工具。但我们自己呢?当我们放弃去思考职业和生活的真正意义,而只是用对就业有用或者无用来权衡自己,权衡自己对知识的汲取和专业的选择,是不是也同样是将自己客体化和工具化了呢?
所以在这篇给新入校的大学生的文章里,我还是不合时宜地写下了理想主义,我也真的希望依旧能在新学期的教室里看到新生眼里的光亮,看到他们想要追寻正义和改变世界的信心和勇气。这个光亮会一直支持你在这条法律之路上坚毅地走下去,并真正获得关于人生最笃定的意义。所以,年轻人,如果你真的对正义公平有渴望和追求,也真的对具体人的苦难有共情和理解,那还犹豫什么呢,法学院欢迎你,这条正义之路也会有无数人跟你一起走下去。
撰文/赵宏
编辑/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 穆祥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