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蛊”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事象,影响深远而广泛,却总是讳为人谈。远古的甲骨文卦爻或易象卜筮典籍里,每每提到“蛊”字;汉代因宫廷权力之争而引发的“巫蛊之祸”,数万人死于非命;延至20世纪,不少人类学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时注意到巫蛊现象,处于当地社会结构中弱势地位的女性,常常被以各种理由指认为巫女,遭到迫害。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远古而迷信的巫蛊现象,在崇尚科学、理性的现代社会并不罕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种种巫蛊或准巫蛊行为仍然以不同面目出现,比如常见的打小人、石狮子、8字车牌、“搞玄学”,巫蛊现象与时俱进,既以另类的方式抚慰人心,又潜藏着巨大的破坏力。
巫蛊从未远去,一直在我们附近。如果说巫蛊是一种无稽之谈,那么为什么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它一直存在呢?这种系统地隐藏在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中的东西,反映了一些什么问题?
6月20日19:00,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邀请了人类学家邓启耀与项飙,围绕新近出版的著作《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讨论这种非常态的精神状态和群体迷乱,及其对于现代社会的警醒意义。活动由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刘亚光主持,以下为对谈精华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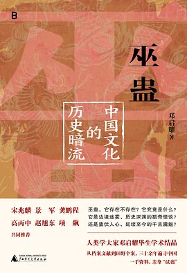
《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
作者: 邓启耀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
2025年4月
整理 | 刘亚光
指认巫师的心理逻辑
刘亚光:《巫蛊》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支暗流——巫蛊。巫和蛊这两件事情本来是分开的,邓老师把这两者合在一起,希望探究中国历史上一些非理性思想的源头。整个研究基于邓老师扎实的田野调研。所以,这本书提供了一些我们平常很陌生的经验案例,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大家受所谓的现代科学、启蒙主义影响非常深刻,但在我们每个人脑海当中,其实非理性思维模式一直是存在的。比如,我们当下看到,年轻人中就正在盛行玄学热。
这本书距离首次出版,过去了整整25年。邓老师研究巫蛊,也有30多年了,是非常漫长的研究历程。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巫蛊这样一个相对冷门的领域视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邓启耀: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民俗学家刘锡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昌仪、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宋兆麟三位教授组织了一套书,邀请我来写黑巫术方面的一本。他们知道,我这个人胆子大,又对文化、心理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因为是老师布置的工作,作为学生,必须认真完成。开始之后,我才发现这工作很难。人类学研究强调田野调查,不能只是从文献出发,所以我七七八八做了两三年。1993年拿出初稿,1994年一个出版社排好版,准备要出版了,但是我觉得不满意,因为觉得田野还没做够。正好在这个时候,主编马昌仪老师的一本研究灵魂信仰的书临时出不了,我听说这个消息就说,那我陪老师,我也不出了。
又过了几年,我遇到了一些很特别的案例,补充了一些田野调查。由于参与观察了精神病学专家对我介绍的中蛊病人的治疗,我得以读到一些跨文化精神病学的书,读过之后豁然开朗。我觉得,医生面对的是个体的“非常意识状态”,这在精神病学中已经有了清楚界定和治疗方案,而人类学面对是群体性的“非常意识形态”。群体发生这样的事情,非常值得关注,它反映的是我们文化心理深层的群体性问题,它会导致社会性的症候。这种症候其实屡见不鲜,比如民俗上的打小人仪式、政治上的汉代巫蛊之祸。而在浩劫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类似事情,比如把人的名字打叉、倒置,等等,这其实都是典型的巫蛊行为,却成为喧嚣一时的社会潮流。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就这么一直做了下来。

邓启耀,曾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退休后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佛性如风:中国佛教艺术研究》及民族服饰系列著作等。爱走野路,曾任中国探险协会副主席。
刘亚光:邓老师刚刚提到,巫蛊心理是一种很复合的现象,它除了是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从个体扩散到整体。项飙老师平常的关注可能和邓老师的研究主题本身稍有差异,但也和社会文化高度相关,您对巫蛊这样一个相当复合的现象,有什么自己的观察?
项飙:我最大的感触,其实是以邓老师为代表的老一代学人的敬业精神。巫蛊当时应该是一个非常边缘的现象、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课题,邓老师愿意做这么长时间。刚才邓老师讲这本书出版时候的风波,他说“我陪老师”,老师的书出不了,那我也不出了,这种意识,可能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虽然这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觉得非常重要。我的老师之一孙立平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他在东北插队的时候,跟着他的师傅骑车,师傅碰到一块石头,车跳了一下,后面跟着的年轻人,也要冲着这个石头骑过去。因为师傅都碰一下,你也得碰一下。当然这个现在听起来有点可笑的感觉,孙老师也不是让大家机械地模仿这个事情。这个事重点是给人一个感觉:“我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这个群体的共同性、公共性非常重要,它超出了我个人的舒适、方便、成就。我们今天可能更多是对上级的服从,是在权力关系明确下的一种义务,但是没有这种自愿地跟其他人形成一个共同体。
邓老师刚才提到两个角度,一方面是有的受害者觉得中了蛊,这种想象,有的时候是因为对于外在情况不能把握,他会认为他的抑郁、焦虑是中蛊。甚至他会利用中蛊的说法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另一种受害者,也是这本书里面最打动我的,就是那些被指责为养蛊的人、被指责为巫师的人。他们中很多人是女性,没有办法跟其他村民正常交往。这个几乎是全人类共通的现象。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对于巫术、巫师的处罚,大量也是妇女。这些被指责为巫师的人,大部分也跟医学有关,比如接生婆、草药师,他们平常是可以照顾别人的,但是突然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巫师。一旦被指认为巫师,爱护生命的接生婆瞬间就变成了下毒手的人,下场很凄惨。
邓老师最后讲到巫蛊的衍生表现。这些做法看起来跟传统不一样,但是在心理结构上有相似的地方。巫蛊这种特别的归因会导致一种强烈的暴力,这种暴力携带着深刻的冷酷,因为当你把人称为巫师的时候,这个暴力就不是暴力了,而是成为正义——“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邓老师的研究,给我们思考更普遍的恐惧、暴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1995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完成本科学习,1998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等。
“猎巫”现象为何长期存在?
刘亚光:的确,很多人指认某人是巫师,可能是出于权力斗争、利益争夺的目的,这个心理古今中外各个地方都存在。项老师刚刚讲的中世纪猎巫是典型,另外一位人类学家王明珂老师,在研究羌族的时候提出的“毒药猫”理论,说村寨的人会找“毒药猫”,为了维持这个群体的纯净性,也和指认巫师有几分类似。不过,在这些相似性之外,邓老师觉得巫蛊现象和它们相比,有什么特殊性?初次出版过了25年之后,您对巫蛊这个问题有哪些新的思考?
邓启耀:这个事情我在书里也谈到,本来我希望写完这本书,巫蛊这个事情就结束了,结果到了21世纪也结束不了。今年初,我还接到湖南的一个电话,一个人自称中了蛊,要我帮忙。他说放他蛊的人已经死掉了,帮他治蛊的巫师也死掉了,他没办法,只好通过互联网找办法,发现中山大学有个人研究这个问题,就打电话来要求我帮他治疗。我劝他:第一,我不会治疗,我不懂这个。第二,据我调查的所有案例,没有一例是真实中蛊的。别的不说,我自己就试过到放蛊人家,吃他的东西,发现没什么变化。我倾向于认为中蛊更多是处在特定文化情境里面才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以,我劝他不必找莫名其妙的偏方,最好就找正规的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病学的专家治疗。医学相对来说,还是有病理性的诊治指标,再不济有药物可以控制。像“跳大神”之类传统的心理治疗,可能也会起到作用,但不可预测。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其实都是小问题。越往深处研究我越发现,巫蛊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现象,从甲骨文时代就有记录。那么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到现在21世纪了,高科技时代,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存在?现在互联网上,包括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媒体上面,很多人讨论问题还是巫蛊思维,而且这些人的学历不低。对于他者的无限猜忌、妖魔化、找替罪羊,成为一种获得心理安慰的方式。更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在身体上侵犯人家,导致类似猎巫的情况。这种群体性的现象,如果在小圈子里面还可控,若成为一种国家化的邪教,比如纳粹;或是当下我们看到的一些恐怖主义思维,怀抱着某种信念,认为这样做是在清洁人类,追求更长远的福祉,就会十分可怕。

电影《女巫》剧照。
项飙:我其实没有太多注意网络上类似巫蛊文化的表达,但我知道大家对神秘现象的情绪是在增加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区分,我认为有必要提一下。“巫蛊”其实是一种指责和归因的方式,不单是一种神秘体验。神秘体验、神秘现象非常多,甚至可以说在社会上永远存在。比如它可能和气候、流行病有关。但当我们用“巫蛊”这个词的时候,并不是客观地在描绘这样一种体验,而是要去排除一个具体的人。没有一个人自称自己在“养蛊”,只有想把你排除出去的人会指责你在“养蛊”。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邓老师书里谈到的很多被指认为巫师的人是女性,或者是平常担当照护角色的人?这些人常常是无权的,本身在社会结构里比较边缘,更方便被指认为巫师,然后被指认为巫师后就更边缘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理论家认为,这种欧洲猎巫现象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有关。
如果我们简单把这个事情看成一个文化现象,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围绕巫蛊有这么强烈的矛盾。邓老师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巫蛊不是一种简单的迷信现象,背后有一个结构。就像乾隆年间的“叫魂”现象。民间说有人叫魂,皇帝说这背后肯定有人做鬼,都是要找出坏人这种归因方式。如果没有坏人,一切都是正常,关键就是有坏人,这个坏人一定要找出来。
如何与“迷信”对话?
刘亚光:邓老师的书里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巫蛊现象的另外一面——它很多时候也可以成为一种弱者的武器。在社会结构里,强势群体之间的争斗,更多可能以权力斗争或者军事斗争的形式体现,是非常显化的冲突。但是,如刚刚项老师提到的,社会的一些边缘群体,巫蛊有时候成了他们向强势群体斗争的武器,因为人们也是害怕蛊师的。
邓老师提到他曾经给一个人看过蛊,这里面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有关对话问题。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来说,邓老师和这个声称自己中蛊的人之间有着巨大的话语鸿沟。这是两种很不一样的观念体系的对话。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困难,但也会有一些产生人与人之间新链接的可能。包括我们知道,项老师这几年在国内媒体上谈过非常多的有关交流、沟通的话题,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观念体系差异巨大的两个人之间的对话的这种困难性,以及这种对话的价值?
项飙:人和人的交流,有时候看起来是两个差异很大的人,但不一定实质性交流的效果就不好。邓老师书里写他到一个被指认为巫女的人家,那个家里没有男人,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女儿,邓老师去她们家吃了一顿饭,家里那几个人是特别高兴的,因为平时一般没有人跟她们接触。一个被指认为养蛊的,和一个大学教授,外人怎么看都觉得是差异巨大的,但却在那一刻有共鸣。相反,现在我们常说的聊得来、容易交流的人,可能也只不过是我们被一个统一的话语系统所统摄,共享一些符号,但是你真的懂我吗?你在乎我的感觉吗?在一个公司里面,在一个学校里,这些真不一定。只能说,我们交流的符号越来越现代、高效、统一,但实质性的交流可能是越来越少的。

电影《女巫》剧照。
刘亚光:这个确实很有意思。邓老师书里面讲他自己刚开始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中蛊的感觉。我想到赫胥黎之前也把自己吃毒蘑菇致幻之后的感觉写成了一本书。把这种神秘体验讲述给读者,我觉得这种对话的鸿沟过于巨大。所以想问邓老师,我把这个问题再聚焦一下:您在研究中蛊的现象遇到的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或者说您有感受到这种交流的鸿沟吗?
邓启耀:我这个人不信邪,所以当时研究这样邪的东西最大的困难确实就是“隔”。但是也因为我不信邪,所以不容易被各种暗示所迷惑。有优点也有缺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的学生做田野调查的时候,都是到不同民族当中,语言不通,生活习惯、文化习惯都不同,老师的解决办法,说起来有一大套,但是做起来就一个字——诚。你只要对人有诚意,不管什么语言,什么群体,都会多少感受得到的。通过对你言行长期的观察,他会知道你这个人可交不可交、可说不可说。有这样一点,你就可以打破很多鸿沟。
我觉得最奇妙的人和人交流的就是人心之间的感应,有些人彼此处得很近,但是心是很远的。有些人可能千里万里,天南海北,但是一旦交往,完全是相见恨晚的感觉。人如何跨越“隔”,真诚地交流?跨文化怎么交流?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所以才有那么多纷争。而且,很多事情也是没有办法说道理和沟通的,所以,只能是让我们尽可能回到一种常识的状态。我非常感谢的一点,是我当知青的时候,少数民族教育了我要回到常识,饿了就该吃饭,想爹妈就应该回家。回到一个正常状态,这是走进人心的前提。
我想到在怒江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当地人都说那个地方鬼很多,两边的山头、峡谷里面是不同的寨子的鬼,所以那个地方老是出事,车翻掉了,人进入太阳没有射到的地方就疯掉了。我这个人不怕老虎,过去自己也画画,对于视觉的东西比较敏感。怒族朋友描述鬼长啥样,我就十分好奇,想见见,还想对它访谈一下。当时我就跟搞音乐人类学的夫人去亲身考察,她录音,我帮她录像。有天晚上,我的电池没有电了,回去充电的时候要一个人路过那个峡谷。过的时候背脊发麻,白天所经历的祭祀山鬼的仪式都在脑子里面闪现了。我打个手电,觉得有点不公平:我在亮处,“鬼”在暗处,情况不对等。我就把手电关了,把自动相机拿出来,打开镜头,想着真要遇到鬼拍一张,我就赚了,因为迄今为止还没听说影视人类学家拍到过鬼。
当然,我最后什么都没拍到。我做研究到现在,经历了很多事,始终都是在追求,能够让我信服的东西。我们过去太容易轻信,社会上流行一个什么大理论,我们就跟着瞎折腾一通,结果发现很多都是纯粹搞笑的,很多又都如过眼云烟。可能也因为这种经历,就想实实在在说点一是一、二是二的话: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些很难理解的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可能就是“不信邪”的一个好处。

电影《女巫》剧照。
项飙:邓老师说得不信邪很有意思。我在想,现在日常话语里我们用这个词,就是说我愿意亲身试试,哪怕有风险。为什么不信邪的人都是少数?其实大部分人小时候我想都是不信邪的,大人越不让他碰那个东西,他越是要碰。随着年龄增长,这种不信邪越来越弱。“梦比天高”,这个话曾经是非常普遍的——不管是对邓老师说的那种夜间的峡谷,还是跟领导、老师讲自己的想法、观点——都越来越少了。
在日常生活里面,不信邪就是不信邪。但是作为研究者来讲,我们对信邪的这些人充分地理解他,他有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们作为研究者的不信邪和日常生活的不信邪应该不在一个平面上,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给他更深刻的理解。这个就是邓老师做的工作,从不信邪出发,对信邪不是做否定,而是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会信邪。
邓启耀:很对,项老师提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问题,其实研究者可以保持你的立场,但是要理解他人、他文化,这个是人类学常说的文化相对主义,就是可以尽可能地理解他文化、理解他人。但是文化相对主义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而是有一个底线,比如对一些陋俗,比如过去裹小脚,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曾有的猎头习俗,对这种文化现象我们要有自己的态度,起码不可以拿来赞美。所以我觉得文化相对主义也有一个底线。我去做这样的调查,不信邪怎么进入邪的文化场域呢?首先是诚,你只要诚,面对它,不管是中蛊者、放蛊者还是指责放蛊的人,你都很真诚地面对他们,跟他们交换意见,你可以说出你的不同意见。我当年有的东西没写出来,可能也不好写出来,是关于双生子的问题,有些民族生了双胞胎是要杀掉的,他们认为不吉利。按他们的神话解释,双生子属于洪水时代躲在葫芦或大鼓之类容器中幸存的兄妹,龙凤胎就是劫后余生成婚的兄妹,生龙凤胎相当于祖先回来了,要发生大的灾难。还有一种解释是认为人只能生一个,猪才生一窝,等等。这是他们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理解他们,可以跟他们谈,我们巴不得生双胞胎呢;他们也会理解你,说你们的风俗是这样的,但我们的风俗是那样的。在这种状态下确实存在一种矛盾,怎么相互理解的问题。我们作为研究者来说,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把事实了解了,至于怎么讨论它,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讨论,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但是我们研究者不是无底线的,而是有个基本的态度,它基于一种普遍的价值。我们人和人之间不可能实现天下大同,但是我们在某种常识下面,大家能够过好日子,健康平等地相处,这个基本的共识是要达到的,大家可以文化不一样,不同而和。
如何看待现代社会的“玄学热”?
刘亚光:邓老师说他是一个不信邪的人,要研究一个邪的东西,所以他很敢。这很有趣。我观察到身边很多朋友,尤其90后,他们有一个心态,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不迷信的人,但是对于很多迷信意义上的禁忌,其实非常看重。如果他们看了算命先生,其实会非常重视对方讲的话。比如有一个算命先生告诉他说,你未来两周之内要做哪些事,否则可能会有血光之灾,或者是遭遇一个感情上的不顺。很难有人会忽略这句话。就像邓老师说的,每个人都说自己不信邪,但是到了让你走入山谷的时候,又没有人敢走。迷信的这种魔力,似乎完全不会随着科学、教育的普及减弱。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讲讲自己的看法?
项飙:这里头两个现象,就是信和怕:你不信这个事情,完全可以搁置,为什么怕它?他说不信,也是真的,不是在撒谎,确实不信。但是这个不信之外,你另外又觉得有一种力量可以控制自己,这种心态其实非常普遍。你问大家,读书有用吗?可能很多人觉得做这个事情没有意义,没有幸福感,或者不知道有没有意义。但大家都会百分百认真地去做。
邓启耀:我今年73岁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几十年过去,什么“鬼”都见到过,碰到任何装神弄鬼的事都会保持一个警惕,问个为什么,而且要探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未知的现象,没做过的事,没见过的都想见一下。当然,可能有一些东西我没见到,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存在,因为有很多未知的东西需要探讨。我主张要对这些事保持尊重。而且同一件事,真的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本命年,家人让穿红内裤、系红带子,这其实是家人爱的表示。每年清明我们祭祖,要烧香,烧一些纸钱,那些纸钱有很多上亿的面值,如果你还是用理性的角度去想,会觉得荒谬,那里不会通货膨胀吗?但我们还是要随俗去做。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们尽孝没有做得很好,大家都在忙,结果子欲养而亲不待,那种遗憾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寄托一下。包括我做佛教艺术研究的时候,不管和尚还是信众,我都充分地向他们请教问题,从他们身上我也获得了另外一种看世界的方式,这是学术、科学以外的一套话语系统,这套系统,也让人看到人类的精神世界确实丰富无比。

电影《女巫》剧照。
刘亚光:邓老师说的也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视角,就是很多迷信行为,其实也可以从一个个体的亲情视角来看待。其实我们当下年轻人的玄学热,算命、塔罗或者紫微斗数等等,还有非常庞大的体系的宗教信仰,以及邓老师书里面研究的流传在西南地区的巫蛊,它们都算是非理性活动,都是在现代科学体系之外的,但是它们之间有很明显的区别,是一个多层次的状态。今年DeepSeek大模型出来之后,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些年轻人在DeepSeek让人工智能给他算命。年轻人会用一个非常理性的现代科学的东西,寻求一个非理性的诉求,现代的网络技术,为非理性的思维和行为可能提供什么样的土壤?
项飙:“理性”是一个外来的词,可以指rational,也可以指reasonable,两个是很不一样的,汉语都可以叫理性。一个人说我要彻底理性,只要分数好,只要把人的关系搞好,只要把任务完成,其他一切都不用管,这个是高度理性的,但是不合理的。理性,但是不合理,今天很多年轻人生活状态就是在理性和合理之间不好把握,仿佛唯一能够让他安心的就是极端的理性。钻牛角尖,把全部的规划理性化,我一分钟都没有浪费,就安心了。
在欧洲,特别是在纳粹之后,这个反思是很重要的。纳粹的屠杀,极其科学,符合理性和效率。纳粹酿成灾难之后,整个五六十年代西方思想发生非常大的转折,大家看到理性的另一面。当理性变成了迷信,变成了疯狂,就彻底变成不合理。现在的技术条件下,我觉得这个危险依然是存在的。技术背后有大量的利益,也跟特定的政治结构吻合,所以不是一个简单技术问题,涉及我们对整个物质资源怎么组织、对人的社会生活怎么安排的问题。这个安排是应该追求怎么样最高效,还是应该追求合理?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其实往往只能靠人自己去感觉,特别是在跟人不同的互动当中形成,它跟理性不一样,没办法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方式就能自然得出什么是合理。
邓启耀:我们做人类学,一贯的做法都是去做实地田野调查,现在我们还面对一个互联网上的虚拟田野。在这里面,有人以为自己换了名,人家认不出来,就可以比较放肆地把自己的本相露出来了,所以在虚拟社区,可能比你在田野里得到的东西还更真实。我正好有一次获得了一个管理员的身份,介入了一个网络上的比赛。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人,她以自己的网名出现的时候,是一个乖乖女。但是,为了表示她自己身边有一拨人,她用不同的化名说不同的话,其实都是一个人,你就看到这个人的多面性。我的学生看完我的书以后说,他们也想接着做。我说,干吗再冒那个险呢?你们不一定有机会,也不一定值得,做网络的调查也很好,特别是,他们有这个长处,做网络这方面肯定比我更厉害。
刘亚光:邓老师讲的也是呼应我们第一个问题。项老师提到,可能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不同年代的人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不一样,他们研究的取向和气质也会不同,邓老师已经给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一些更年轻的学者们提出了建议,就是说可以更多利用虚拟的田野。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更年轻的学者对于虚拟世界的经验会更加敏锐。
今天晚上两位老师的对谈,给我们打开了更多的可能,理性与非理性,本身都被需要,也都有其自身的破坏力。我们并不能用单一的价值判断衡量我们身边的这些理性或者非理性、迷信或者不迷信的现象,而是要对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对不同现象的差异保持开放的心态,我相信可能这是今天分享这本书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最有启发的地方。
整理/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
校对/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