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世说新语》是一本快乐宝典,但是什么是快乐,或者说快乐是什么,刘义庆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而是把他想要说的一切都藏在了故事之中,让读者自己去探寻。
《世说新语》的《言语》篇中有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场面: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言语》23)
名士们到洛水边玩耍,回去之后乐广问王衍说今天玩得快乐吗?面对这样简单的问题,王衍的回答非常值得玩味。他没有说快乐也没有说不快乐,而是细数了洛水畔名士们各自清谈的景象:裴頠畅谈了名理、张华说的是《史记》《汉书》,而他自己则与王戎讨论了延陵季子和张良。
于是问题来了,王衍觉得快乐吗?或者说,乐广听了王衍的回答之后知不知道他快乐还是不快乐?当然,根据王衍的回答我们可以推测说王衍是快乐的,前提是王衍爱好清谈,他应该享受了清谈的过程。可是对于有些内向而不喜欢社交的人来说,参与了一天的清谈,是不是会觉得疲惫而无趣呢?于是问题又来了,乐广快乐吗?乐广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他自己感到不快乐呢?如果他也感到快乐,为什么还要问王衍快乐不快乐呢?
上面近乎绕口令般的一连串问题并非在玩文字游戏。它们暗暗地告诉我们乐广对于快乐的两个假设。第一,快乐是主观而没有统一标准的——同样在洛水之滨玩耍,可能有的人感到快乐而有的人不快乐。若是乐广快乐王衍也必然快乐,他就没有必要发问;反之亦然。第二,我们是无法知道他人是否快乐的——即使在别人看来王衍谈得口若悬河,他也可能内心并不快乐。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选自《未尽的快乐》,部分注释从略,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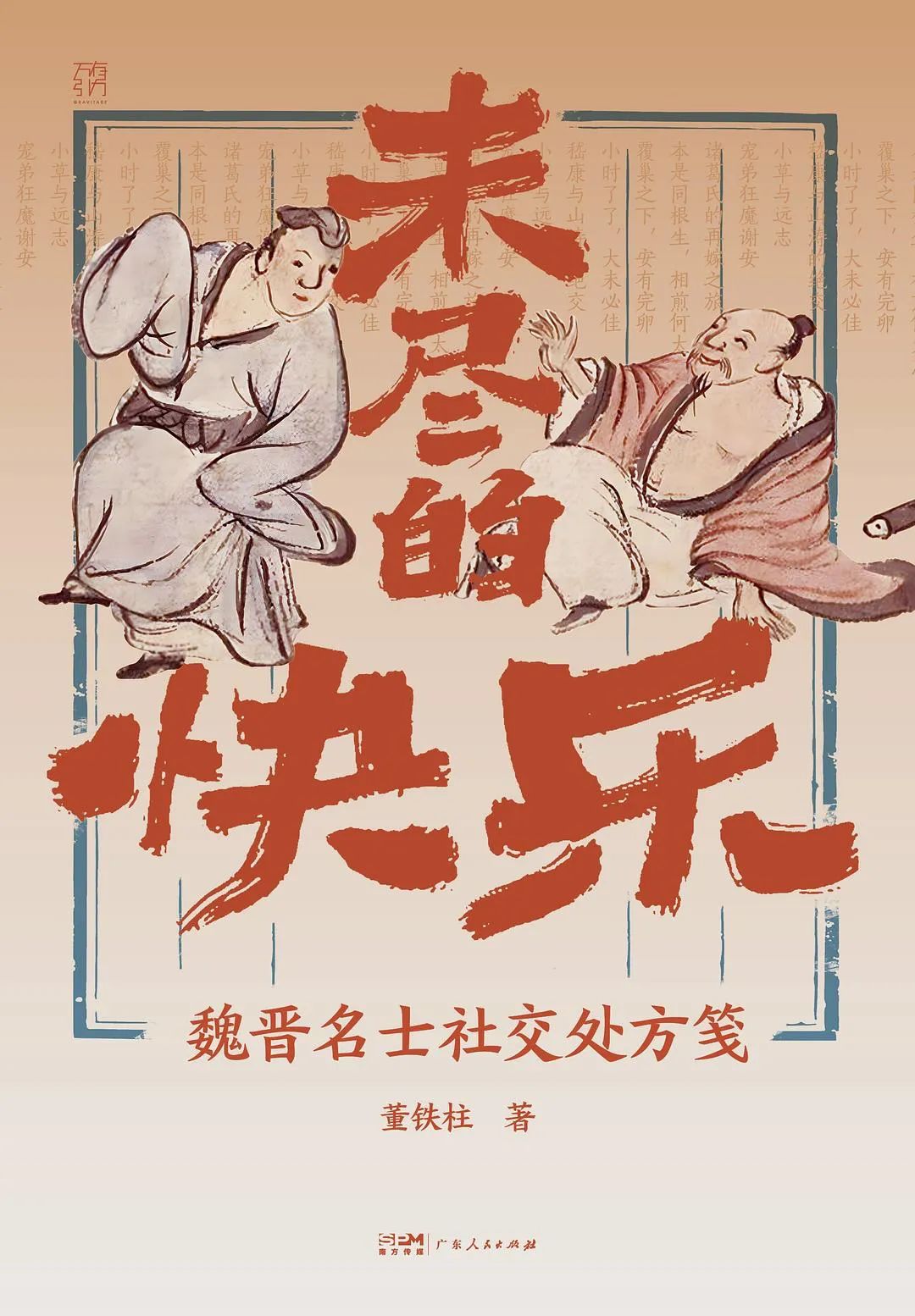
《未尽的快乐:魏晋名士社交处方笺》
作者:董铁柱
版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5年5月
老子如何看待快乐?
不按照自己本性的生活会怎样呢?有一次太尉陆玩去拜访丞相王导,王导拿奶酪招待他。陆玩回家就病倒了。第二天他给王导写信说:“昨天吃奶酪稍微过量,整夜精神萎靡,疲困不堪。小民虽然是吴人,却几乎成了北方的死鬼。”陆玩是南方人,他的肠胃显然不适应北方的食物,因而他贪吃奶酪不顺应自己的习性,从而导致贪嘴遭罪。可见,普通人要发现自己的本性并顺应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普通人,也就是“俗”人。无论是孔子还是庄子都试图批判一个问题:俗。庄子在《至乐》中反复表明俗是自己的对立面;虽然孔子没有明确提到俗,但是他经常提到的“小人”基本与俗人相似,而他所说的小人甚至包括了自己的弟子——既然连弟子都可能不理解孔子的快乐,那么遑论他人,因此对孔子来说世上也同样充斥着俗人。孔子和庄子的快乐观尽管存在着差异,不过在对“俗”的批评上双方的立场却惊人的一致。对于孔子来说,俗人无法安贫乐道;而对于庄子来说,俗人不能顺应自然。
如果老子看见孔子和庄子,那么他估计会给他们细细讲解一下《老子》第八十章。在其中老子说,一个理想的社会会让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乐其俗,就是让大家以自己的习俗为乐,或者说在自己的习俗中找到快乐。和圣贤相比,“俗”人是大多数的存在,习俗对俗人来说是约定俗成的生活规则。老子的意思是要尊重百姓们的习俗,这样的观点与孔子和庄子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电影《孔子》剧照。
在孔、庄二子眼中,俗人都不真正懂得快乐。如果说孔子渴望改变百姓的习俗,让他们成为君子从而感受到孔颜乐处,那么庄子则连这个企图都并不强烈——既然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本性,那么俗人可能根本无法改变。不过严格来说,庄子依然怀着改变俗人的愿望。《至乐》中庄子和列子分别遇见骷髅,骷髅对两人都进行了劝说,这表明骷髅并未放弃教化他们,而庄子丧妻后的鼓盆而歌也证明他接受了骷髅的观点。相比而言,老子则完全没有想要改变俗人之乐的意思,相反,他认为不但俗人之乐无需改变,而且需要得到肯定。那么,什么是《老子》所谓的俗人之乐呢?
汉朝的《老子河上公章句》把“乐其俗”解释成“乐其质朴之俗,不转移也”。所谓质朴,也就把孔子所推崇的礼仪排斥在外;而“不转移”则强调了无须教化或是改变。河上公的解释指出了两个关键之处:一个是普通百姓也许不听从圣人的仁义礼法,可是“质朴”的习俗对他们的调控可以确保他们做事的底线;另一个是大众的习俗可能与精英或是圣贤的观念有着明确的抵牾,但是在老子看来,圣人就是圣人,俗人就是俗人,两者都是社会必要的组成部分,俗人没有必要变成圣人——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圣人就是社会的统治者,俗人就是百姓,两者皆不可或缺,要是社会上没有了俗人,人人都成为君王,社会也就乱了套。
王弼把河上公所说的质朴之俗概括成“无所欲求”,这看起来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应和了孔颜乐处和庄子之乐——孔子、颜回和庄子也不以追求物质欲望为快乐。但重要的是,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俗人“无所欲求”可以理解成俗人不奢求成为圣人,而是满足于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因而“乐其俗”的关键是相对固定的人际关系。众所周知,老子所推崇的质朴习俗有一个前提:小国寡民。小国寡民意味着一个国家内部的人际关系非常稳固而不复杂。在一个与相望的邻国百姓都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是熟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而在熟人社会中,稳定的关系是最显著的特点。费孝通曾指出相对封闭的中国乡土社会中“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费孝通所说的“同一的意义体系”,也就是老子的“俗”。事实上,费孝通也指出在人际关系稳定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无为政治”,因此老子哲学中绝对封闭的社会会更加依赖伦常中的各种关系。所谓的无欲也好,质朴也罢,都需要在固定的人际关系中实现。可以说,老子“乐其俗”的主张比孔子和庄子都强调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尽管孔子对人际关系的重视早已人尽皆知。

电影《孔子》剧照。
何谓“乐其俗”?
在相对简单而稳定的人际关系中,抽象而理想化的哲学思想失去了用武之地。百姓在乐其俗的同时并不需要哲人的指引,他们的习俗完全来自于自身的生活实践。也许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理论来解读老子所说的习俗。布迪厄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阶级是区分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决定性要素。布迪厄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作了发展和补充。他认为仅靠阶级这一要素无法完全解释不同阶级各自所具有的思想与行为。于是,布迪厄提出了“惯习”这一概念(虽然habitus通常译作惯习或是习性,但是惯习一词多少带有翻译的生硬感,因而接下来我们还是使用更符合中文语感的“习俗”)。
在布迪厄的理论中,习俗是一系列特殊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因而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层面。它不像哲学思想那样抽象,而是实实在在指引着人们的行为;于此同时,习俗并不是被所有人都普遍接受的,恰恰相反,它的重要作用在于对群体作出区分,这意味着某一种习俗只会被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所接受,而接受某一习俗的这部分人则可能会和接受另一习俗的那部分人划清界限。
那么,习俗是如何形成的呢?它来自于社会结构的影响,而所谓社会结构的影响,其实就是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力量。一个人出生之后,就处于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愿而存在的客观关系之中。不同的父母会带自己的孩子去他们感兴趣的教堂,让孩子上他们觉得合适的学校,让孩子听他们喜欢的音乐……于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下一代就会接受父母所传承下来的习俗,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也就会得以延续。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社会结构产生了习俗,习俗决定了人们的实践,而实践则会再巩固与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因此,在社会中关系和习俗是一对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概念。布迪厄的理论是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并且他把习俗视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文化资本,用以区分不同的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布迪厄所说的习俗和汤普森的“习俗”(custom)有相似之处。两人均通过习俗来强调阶级之间的不同文化。汤普森在平民和贵族之间划了一条鸿沟,而在布迪厄看来,法国存在着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三个阶级,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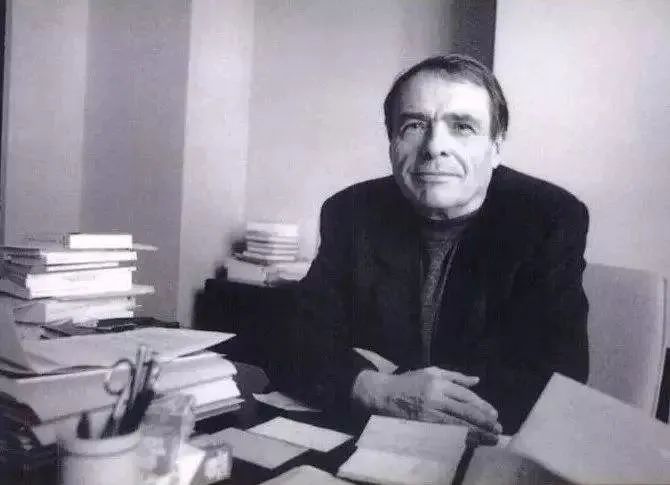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
不同群体的“俗”
我们借用习俗这个概念,并不需要纠结于他们理论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元素,这些当然不适用于魏晋的社会。我们借用“习俗”这个概念,是为理解“乐其俗” 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理论依据。如前所述,王戎把人分为三类:最上等级的圣人,最下等级毫无情感的人和在中间的普通人。王戎的分类和阶级自然毫无关系,而是沿袭了汉代以来“上、中、下”的人性三分法,他所说的普通人也就是出于中间阶层的“俗人”——他的好友阮籍就曾经戏称他为“俗物”。
三者的区分不是阶级的差异,而是道德境界的不同。如果我们承认王戎是快乐的,那么也许可以说以王戎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就是一群乐其俗的“俗人”。 如此说来,魏晋名士倒是在一定程度了践行了老子的思想。他们把自己定义为俗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找寻快乐。既然俗人的习俗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圣人的观点就无法替代他们的习俗来指引俗人们的实际生活。俗人们的习俗可能与圣贤的主张有所冲突,也可能在道德或境界上不及圣贤,可是当王戎和孙放强调自己不敢企慕圣人时,习俗就成为了他们在乱世处理人际关系最具实践性的指引,而他们也在习俗的指引下获得了快乐。因此,尽管我们对圣人与俗人作了区分,但是绝对不应当否定俗人的价值,而是应当肯定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俗人风俗的价值在于对人际关系的重视。我们知道,《庄子》中的圣人似乎把社会关系视为束缚,而孔子虽然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但是至少在《论语》中他和颜回自身都没有怎么面对夫妻、父子或是朋友等关系的困境——孔子最常遇到的是学生的质疑而已。圣人的境界让他们不纠结于人际关系中的琐碎之处,而是把目光投向更为远大的地方。王戎在遭遇爱子之丧时的话也暗示了这一点:圣人会忘情。相反,俗人反而会更加期望处理好自己与他人的各种关系。乐其俗,也就是以风俗为指引在人际关系中找到快乐。
不过,老子思想中的乐其俗也有着不可避免的问题。在老子理想化的架构中,一个个小国是不相来往的,那么各个小国的百姓必然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习俗。由于他们之间没有往来,不同的习俗之间也就不会引起纷争,如此才能确保他们“乐其俗”。问题是这种过于理想的状态很难在现实中实现。各个小国之间互相封闭的国门一旦打开,大家就可能由于“乐”自己的风俗而觉得别人的习俗不合理,于是争论就在所难免。在《论语》中有一个这样的名场面: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
来自楚地的叶公以自己的习俗为荣,在他们那里有一个正直的人,在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后,作为儿子的他举证了父亲。孔子回答说,他们那里对正直有不同的理解,父子之间做到父亲为儿子隐瞒而儿子为父亲隐瞒,这样才算正直。
关于“父子相隐”,学者们有着诸多的讨论,这不是我们在此所关注的话题。我们所关注的,是叶公和孔子——或者说楚国和鲁国——支持不同的习俗,而他们所争论的习俗与父子关系直接相关。在这个场面中,孔子固然反驳了叶公的习俗,而叶公也并没有被孔子所说服,叶公分明是乐其俗的。这不仅是叶公和孔子的交锋,也是楚国和鲁国两地习俗的较量,更是俗人和圣人之间的争论。虽然两千年来的思想家们不断论证孔子观点的合理性,但是当代学者的争论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叶公的习俗也并非一无是处,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不乏支持者。这表明即使是圣人也难以彻底否定习俗的影响。

电影《孔子》剧照。
即使在鲁国内部,不同境界的群体之间也有着不同的习俗,正如布迪厄说不同阶级有着不同习俗一样。《论语》中还有一个“樊迟问稼”的名场面。孔子的弟子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了。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啊!”(《子路》)皇侃解释说,“小人是贪利者也”。在樊迟的习俗中,学习是为了现实的技能,他不知道孔子教的是仁义忠信之道。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应该有别的老师会教学生教授稼圃等技能,或者说,樊迟的父母带给了他默认的观念:学习是为了解决更好地谋生。正是有支持这样习俗的群体存在,才会确保百姓能够“甘其食”,满足必须的物质生活。
樊迟和孔子的问答让我们想起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他认为传统的宗教关注精神世界,而新教则更多地考虑世俗事务,新教的发展促生了以赢利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精神。我们可以轻松地发现,樊迟的习俗与新教有着相似之处,而孔子则有着传统宗教的影子。把利视为唯一的目的固然不妥,但是考虑世俗的实际生活确实也是不可缺少的。《管子·牧民》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而稼圃正是仓廪实的基础,因此樊迟被这样的习俗所影响也同样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周朝的先祖后稷就是一个种庄稼的高手,《诗经·大雅·生民》就详细记载了他从事农业生产的壮举,谁又敢说后稷所做的一切毫无意义呢!
最玄妙的,也是最世俗的
如果我们像魏晋名士那样视孔子为圣人,那么孔子与叶公和樊迟的分歧就是圣人与俗人的区分。和两千年来批评叶公和樊迟的历代思想家们不同,我们在“风俗”理论的指引下,认为小人或俗人同样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并非要否定圣人存在的意义,而是在肯定圣人理想价值的同时强调不同的俗人群体有着各自的习俗,而他们都能在各自的习俗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这正是我们接下来剖析魏晋名士之乐的出发点——即使达不到圣人的境界,名士的快乐对我们来说也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以想要学稼的樊迟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魏晋名士喜欢李子,不但喜欢吃还擅长种。他们显然“忘记”了圣人的叮嘱,甘愿做一个乐于种植果蔬的“小人”。和峤就是其中的代表。《世说新语》中说,和峤家种了上好的李子树,他的小舅子王济问他要李子,他给了区区几十个。王济颇为不满,趁着和峤不在家,带人拿着斧头到和峤家,先是美美地吃了一顿李子,然后把李子树给砍了。下了狠手的王济还送了一车砍下的树枝给和峤,问他说:“(这树枝)和你的李子比怎么样?”和峤只是一笑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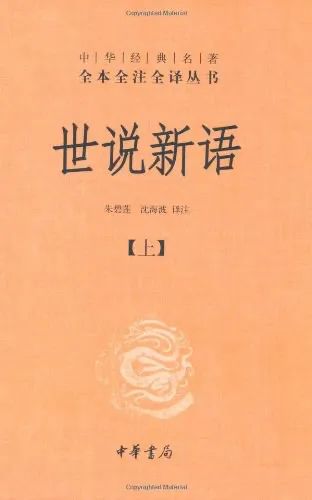
《世说新语》(上下)
作者:朱碧莲,沈海波 译注
版本: 中华书局
2022年10月
这个故事很好地展现了魏晋名士的“乐其俗”。和峤爱吃李子,于是就乐于自己种,这样的快乐非常单纯;他爱惜自己的李子,就宁可背着吝啬之名也不肯多给小舅子;可是,当他的李子树被砍后,他也只是笑笑而已,并没有痛心疾首,隐约有一丝顺其自然之意。同样,王济也爱吃李子,即使姐夫不给也要去抢着吃;虽然对方是自己的姐夫,但是王济也根本就不在意所谓的长幼之序,就是想给和峤一个教训。一场闹剧下来,两个人居然皆有自得其乐之感。
之所以说自得其乐,是因为这个故事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和峤李子树的李子好吃既然人尽皆知,说明应该不是第一次结果。那么,想必前一年甚至前几年王济也向姐夫讨要了李子。按照王济的性格,如果前几年和峤也給得那么少,很可能早就把树给砍了,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前几年和峤給得应该不少,前后对比才引得小舅子的不满。王济的骄横也是名声在外,和峤不应该不了解他的性格,甚至不难预测砍树这样的举动。
最有趣的细节是,和峤固然不在家,可是他的妻子也就是王济的姐姐难道也不在吗,为什么她不出来制止呢?吃李子固然快乐,然而每年都有人来讨要却不免烦人,可是自己又舍不得毁掉李子树。如此说来,很有可能和峤是故意今年少给王济李子,借他之手来去掉它。和峤之举虽说是无可奈何,却让他的快乐最大化。失去李子树而换得宁静,不用再为了到底给不给别人李子而揪心,这对于小气的和峤来说也许反而是一个快乐的结局。
王济的快乐则是显而易见的,他畅快淋漓地给看似小气的姐夫上了一课。这样的快乐当然孔子或是庄子所不屑的,但是却能够真实地打动我们。与孔子和庄子所说的俗人不同,王济的快乐并没有来自与名利富贵,而是一种非常直接而真实的爽快——这种恶作剧后的快意应该是很多人都能心领神会的。如果把这种不造成恶性伤害的恶作剧看作名士间的习俗,那么他们肯定是乐在其中的。
从快乐的角度来说,老子的“乐其俗”给名士们以共鸣。老子思想在魏晋的流行是众所皆知的事实,不过不少人认为这是由于老子哲学玄妙之故。事实上,最玄妙的也就是最世俗的,名士们对老子的喜爱,也许正在于可以把老子思想运用于俗世的生活,可以理所当然地从自己出发,在不受抽象哲学思想约束的情况下寻找生活之中的快乐。
作者/董铁柱
摘编/刘亚光
编辑/刘亚光
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