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从去年11月开始出现,而今愈演愈烈的对文学抄袭事件的争议,终于还是被摆在了更大的公共领域之中,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
这一把火,最初是一个叫“抒情的森林”的网友点燃的,如今卷入漩涡中心的既有孙频这般冲击鲁奖的作者,也有蒋方舟这般早已暴得大名的才女,还有丁颜这样的青年作者,凡此种种。
《人民文学》《收获》《天涯》等刊物出了非常官方的回应,似乎并不能平息众怒。在此过程中,大部分作者对公众保持沉默,所谓正统文坛也少有人对此公开发言。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鉴抄”,也有人认为这是“猎巫”。如何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与之同样微妙的,还有抄袭与借鉴之间的区别。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回顾了这场事件,也回应了抄袭与借鉴的争议。作者认为,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鉴抄”事件,能够一直持续发酵,背后也反映出了文学生态的“失衡”。
1
“抒情的森林”里的风暴
这一事件中,当事人丁颜的回应和评论家张定浩的发言值得关注。很可以作为对此问题讨论的切入口。
我们可以先引证他们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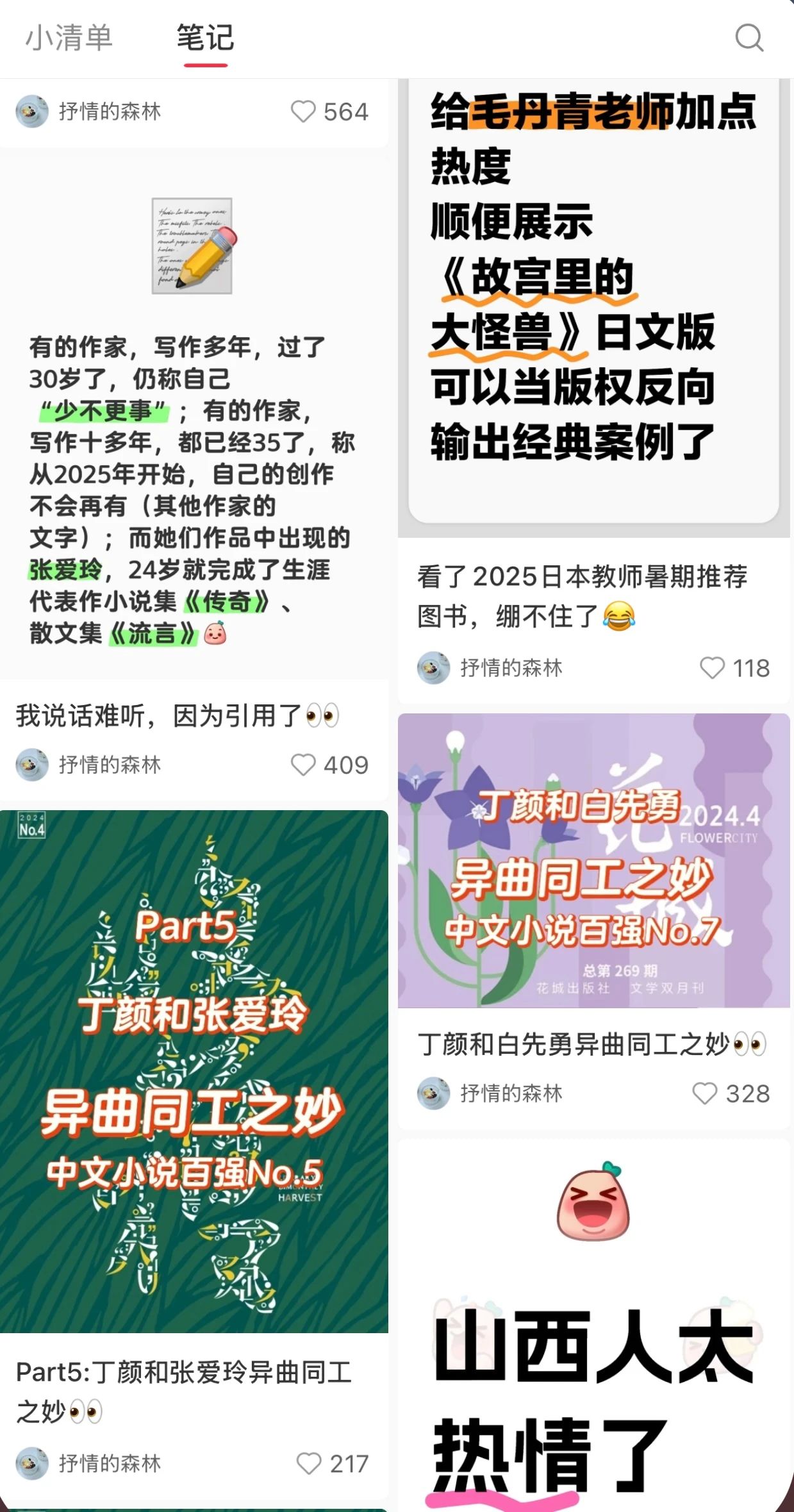
博主“抒情的森林”主页。
丁颜在朋友圈发了一段长文:
“句子查重一致,没有什么不能认的。如果抄袭的标准是:
句子查重一致被认为抄袭,那无可厚非这就是抄袭。
但查重工具只能标红文本,无法阅读人心。如果一致就一定是抄袭,那对大地上所有相似的解读都是在互相抄袭。
抄袭是道德行为,取决于意图——是否故意隐瞒来源。查重工具无法评估写作的诚实或努力。
所以这个查重的读者,你也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读者——用查重,都懒得去读只能说没什么智慧的写作者遇上只认字的读者。我认为的好的文学作品,是行云流水的意象爆发出来的思想,它会让读者脑内颅高燃,是爆发意象,启发新生、希望,而不是苍蝇拨屎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舔,寻找横竖撇捺一致。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是:
一、已经出版的两本小说集,作废。所得荣誉奖品自行销毁。
二、这些作品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左右时写的,与今年才开始教我写作的学校老师一概无关。
三、从今天开始如果还写作,会用笔名。丁颜这个名字已被污染,丁颜已死。这件事不要牵扯丁颜之外的人,丁颜无所谓,但牵扯与丁颜有关,与此无关的人,一定会告到底。
最后想告诉查重的这位读者。别想用这种方法想把我们(我知道这件事只是一个开头,你会没完没了,可惜你不识藏文,我还曾经用藏文写过诗,你查一查可能句子一致的更多)掩埋,因为我还年轻,我自认为我是一颗种子,才开始学习写作,在用尽一切可能的表达方法表达一切。不管是自己造的‘句子一致’的粪土,还是你的这种查重一致的屎料,都只能让这粒种子发芽茁壮。”

《影子写手》剧照。
张定浩先是转发丁颜事件的微信文章,附上一段评论。在丁颜公开回应此次事件之后,张定浩又发了一段评论。
“唉,又一位作家需要‘修辞立其诚’,需要‘用新作证明自己’且迈向‘更纯净的原创’了。可怜这篇我当年排行榜也点评过想起有如今已失去联络的朋友当时就批评过我的溢美之词,我还不以为然。但张爱玲我当时竟没读出来,可见我看书之粗疏,实在是惭愧!”
“一个写作的年轻人犯了错为什么能这么振振有词?没有道歉只有对指出者的痛恨:以及对编辑老师们的抱歉,却没有任何对读者的交代和愧疚。装死圈内部的情谊无价,真让人感动!” 我想先从“抄袭”的性质入手讨论这个话题。这也是最直接,讨论最多的话题。抄袭怎么认定,是否是借鉴、化用、模仿、致敬等。对涉嫌抄袭者的批判是否过度,进而导致了网暴、乃至“猎巫”。
而我更关心的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即为何此番抄袭事件在事发大半年后,才引来轩然大波。我一向回避阴谋论的解释,在此我试图给出一个文学社会学的说明。
2
身份暧昧的“模仿”与创意写作的“隐疾”
这些作家被网友查到在作品中,有不少段落文句与前人作品雷同或相同,这作为事实似乎无可争议。难在性质的认定上,文学写作不是平地起惊雷,总是在一定传统之中展开的,由阅读而来的对于意象、句式、结构等等的借鉴、化用与模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甚至成为一种特定手法。最极端的也许是“集杜诗”了,文天祥把杜甫诗句重新排列组合而成一首新诗。古诗词中陈陈相因,乃至明清之际,作品面目相似者比比皆是。
本雅明有个理想,要写一部全是引文的作品。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结构上模仿荷马史诗《奥德赛》。这种情况在类型文学上可能更加严重,类型文学一般会有相对稳定的叙事模式、套路等。比如侦探小说中的神探+助手(福尔摩斯+华生)模式。不少民国侦探小说中,都有福尔摩斯的影子。很多当代中国侦探小说,则是一股浓浓的日系推理小说味道。中国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与拉美文学具有家族相似性,这是风格与手法上的亲缘性。乃至对莫言、马原等人的评价,都不得不辨析他们的“中国性”,或褒或贬。与之相似的是前几年也引起过争议的“融梗”“洗稿”等现象。
把这些性质、程度各不相同的案例放在一起,只是想说明,在文学写作中,对是模仿、借鉴还是抄袭的区分,有时并不容易断言。

《编剧工坊》剧照。
对此的讨论,还涉及雷同文本的比例问题。我们知道,在学术工业流水线上,一项重要步骤就是查重,而这个查重是有比例的,即你的论文重复率不高于一定比例,比如10%,或20%。作品有少量重复,比例极低,虽有字句相同,是否还要认定为抄袭?语句抄袭还是观点抄袭?所以对抄袭的认定,并不容易。但需注意,文学与学术似乎还有不同。在我看来,浪漫主义关于天才与原创性的神话,使得我们对于文学的独创性有着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于所谓纯文学或严肃文学(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纯文学和严肃文学是伪概念,此处出于讨论方便而用)。因此对于纯文学,而不是开始时候被鉴抄的儿童文学,更刺激大众的神经。

《影子写手》剧照。
丁颜提到“抄袭是道德行为,取决于意图——是否故意隐瞒来源”。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辨析:文句上的相同是出于有意的挪用(不道德的),还是无意间的使用或“撞句”(非道德的)。如果有极少数雷同句,且是不自知的使用,出于习惯,难言抄袭。大量阅读与习作模仿,乃至摘抄好词好句的训练,都使得这种雷同可能来自无意识的使用。特别是考虑到这些作者很多时候重复的是诸如加缪、张爱玲这种“烂大街”的作者“烂大街”的作品。
作为一批极为聪明的人,我想他们大概率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我看到一个解释,说这也许因为这一批作者多有创意写作背景,而创写训练中对经典的模拟是其中重要训练,拟写与创作的混淆而成了此类作品。这些习作,很可能因为写得不错,而流入文学期刊。当然很多时候不是投稿,而是“老师”推荐。在我看来,如此写作习惯,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它的拟写,可能是整体结构上的,也可能是对某些情节、片段的书写上的。在作者是路径依赖,在读者却是抄袭。这是一种巨大的错位。
当然,这是善意的猜测,很可能就是抄袭,在此我不做断言。
3
傲慢与愤怒:文学生态的幻觉
现在,我们需要转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看来,丁颜的回应,触怒张定浩的原因在于她的态度:对读者的傲慢与对圈子的维护。这与其说是精英主义的态度,不如说是伪装的山头主义:“装死圈内部的情谊无价”。丁颜最后莫名其妙的威胁,仿佛在说“我要正告这位读者”。正告这位读者,你对“我”的批判,不会影响圈子对我的维护,当然,这种维护是通过一种自我奋斗的神话来表达的。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本来处于道德低位的人,却站在道德高位指责披露者,并且隐秘地征引了“告密”这一令人惊恐的意象。试图以此把自己放在受害者、奋斗者与真诚者(通过部分的忏悔的实现)的位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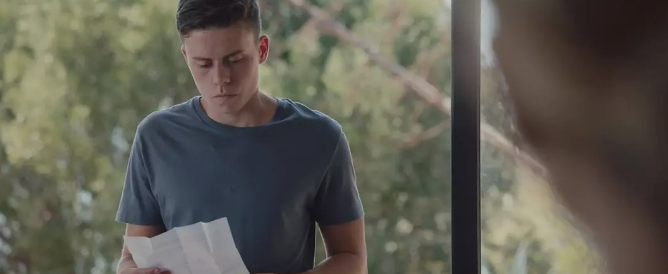
《编剧工坊》剧照。
但这与其说是道德的宣告,不如说是权力的宣告。这般转化能够如此自然地发生,乃是因为文学圈子的特权化。宣告普通读者只配接受她的作品,而不能审判她的作品,她的作品只有“圈子”能够审判。而正是这种态度才是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在之前的文坛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很少如此赤裸地表达。主流文坛的圈子化、封闭化,乃至于世袭化,使得文学圈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门阀,它们的生产与评价,乃至斗争,都是门阀内部的事情,普通人不能参与其中。普通人的指责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配不配的问题。正是因为不配,让她感到冒犯,所以她才要正告读者,不要越界。这不仅是文学天赋的问题,更是文学话语权与文学生态的问题。
对此权力表演的不满,就表现为对此番涉嫌抄袭的作者海啸般的围攻。在现代文学神话中,浪漫主义只宣称了文学天赋的重要性,而在我们则异化为文学话语权上的特权。更复杂之处还在于,现代文学权力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传统文坛代表的文化权力,一个是市场的权力。现在的处境是,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时代,纯文学已经边缘化,另一方面纯文学又占据着某种文化资本与权力,这种交织使得纯文学圈子处在极其尴尬的位置,其文学权力上的特权具有某种虚假性。因为读者已经获得了某种审判权,无视这种审判权,就表现为傲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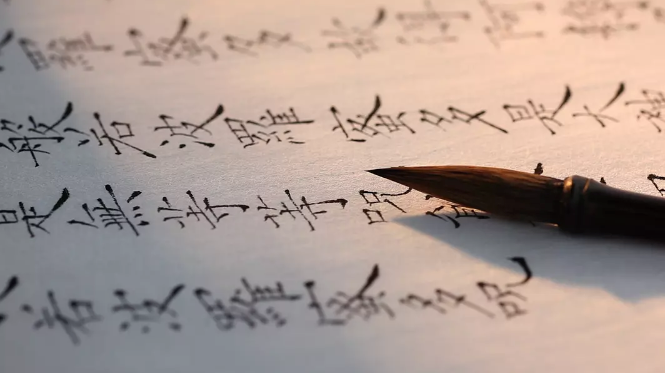
《他们在岛屿写作》剧照。
而对这种权力的意识,就使得她“正告”读者时,也带着战栗与恐惧:“这件事不要牵扯丁颜之外的人,丁颜无所谓,但牵扯与丁颜有关,与此无关的人,一定会告到底。”丁颜之外的人,我们会想到丁颜的导师余华、文学杂志的编辑等等文坛内部的人。实际上,大刊似乎也没有对此给出明确而具体的回应。在此沉默就是保护。这让我想到文二代在各类文学顶刊轻易登场。此类文二代迭出,也是这种文坛生态的表现。创意写作班是另一种文学代际生产的方式,但也表现出门阀化的倾向,比如名校化与高学历化,而名校与高学历教育中“寒门”比例在减少,也在创意写作班中有所表现,使得门阀化的局面更加复杂和严重。
某些读者在此表现出的“暴力”倾向,不能简单视为猎巫(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抒情的森林”揭露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女性),或者群体暴力的历史重现,而应该视为对不平等权力表演的非理性反抗。在此单纯指责这种非理性暴力,不仅是伪装成理性的傲慢,更是对权力固化的掩盖。
情势滔滔,不仅是对抄袭的不满,更是对文坛固化的不满。毕竟刚开始的批评指向儿童文学这一在纯文学边缘化的领域时候,并未引起太大风波,而当抵达纯文学的核心地带时候,就引起了风暴。而对此问题的解决,则期待于对文坛生态更大的变革。
撰文/黄家光(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编辑/刘亚光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