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呼唤叙事的复归时,微观史大家金茨堡(C. Ginzburg)曾尖锐地批评过往的历史学道:“自伽利略开始,自然科学的定量和反人类中心的方法使人文科学处于令人不快的两难境地:要么使用弱的科学标准,能够获得重要的结果;要么使用强的科学标准,获得不重要的结果。”确实,在科学导向下历史主体处于休眠状态。作为中国微观史研究的重要学者,王笛的《中国记事》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他者”(other)的视线。幽闭在洞窟中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倒影,他者的视角不仅能弱化本质主义叙事带来的沉闷,还可以提供重新认识自他关系的契机。王笛擅长绘画,曾在自著里展示过所绘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海登·怀特、费正清等十九位历史学家的素描,惟妙惟肖。王笛绘画的本领也反映在本书的叙事上,《中国记事》八部二十九章,仿佛手绘的一张张卡通片,连缀起一部别样的分叉的历史。
撰文|孙江(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讲席教授)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学人分为两个类型:刺猬和狐狸。前者一以贯之,是一元论;后者灵动善变,属意多元。伯林以结果论学人,竟发现自己无法归入任何一类。在我看来,如果按照学者的作业方式,似可分为如下两个类型:农耕型和游牧型。农耕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品如醇酒,历久弥香;游牧型逐水草而生,苟日新日日新,我变故我在。在我熟悉的学者里,王笛无疑属于农耕型,晨起即书,两小时后方才洗漱早餐。正是如此勤勉不懈,王笛每有新作问世,或聚焦四川,或深描成都,写到快与研究对象同一化成了“四川王”或“成都王”。王笛是那种待在房间里可以一个星期不出门的学者。四川人嘛,只要有麻辣,吃啥都一样。
不过,翻阅案头散发着油墨香的《中国记事》(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的看法稍有动摇。这本“跨出封闭的世界”——不以四川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凡八部二十九章,从1911年辛亥革命写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928年,也就是说,涉及绵延二千余年的皇权统治的坍塌到现代党国体制的确立这一时段。这是一个不安的时代,被称为军阀混战;军阀割据不假,混战实为夸大之词,因为军阀之间很少真枪实弹相向的。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思想、文化、经济乃至政治充满了多种可能性,我一向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确切地说是北京政府时期——堪称中国现代文化的“轴心时代”,形塑了现代中国的轮廓,换言之,现代中国的基本命题都可从这一时段中找到。惟其如此,这段历史犹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的“分叉的历史”(bifurcate history)的临界点,值得学者深描细述。
“比胜利更伟大的是中国的觉醒”
《中国记事》的第一部由三章构成,写辛亥革命后美国人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观察。了解电视连续剧文本结构的人都知道,第一集十分关键,主要人物不仅要登场,出场的方式也很有讲究。本书第一章在铺陈上颇下了一番功夫。教师司徒雷登、军官史迪威、商人约瑟夫·克根、清朝四品大员濮兰德和美联社记者德里克·麦考米克等依次登场,他们对中国现状表达的同情的理解奠定了本书的格调。正因为有如是舆论环境,1913年威尔逊甫任总统即宣布承认中华民国,使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美国开始深度介入中国问题,以维护中国统一为基本方针。与此相对,日本为防备列强妨碍其扩张的野心,提出了“国际共管”主张,试图获得在中国权益的最大化,如此美日之间的交锋不可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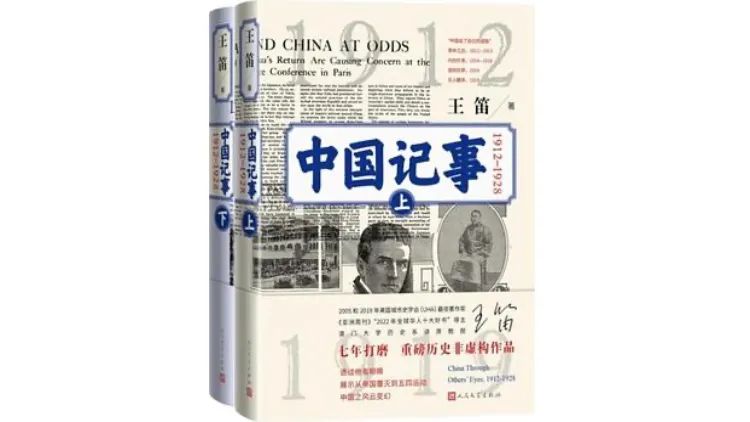
《中国记事(1912-1928)》
作者:王笛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5年4月
第二部五章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美日之间围绕德国交还山东权益的博弈。中国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收回胶州,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个友好国家的使节”。这位“中国真正的朋友”激烈地抨击1915年出笼的《二十一条》。欧战原本是中国争取独立的机会,如《字林西报》财经编辑司瑞尼瓦斯·威格尔所说,中国犹如被几个混混群殴的人,由于混混们突然自己打了起来,得到了站起来的机会。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被冷遇说明还没有真正站起来,这是后话。第二部分着墨较多的是袁世凯称帝前后的情况。辛亥革命被一些美国人视为“一场在中国发生的美国革命”,因此舆论对袁世凯称帝普遍倾向否定,王笛着重考察了袁世凯的支持者——人所共知的古德诺的意图。
第三部五章写1919年巴黎和会前后的博弈。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当收回被德国攫取的权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这让中国抱以很高的期待,但最后重重的落空。王笛引用塔奇曼的话指出,巴黎和会让中国看清了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外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看似偶然,实则有帝国主义国家间利害交换之必然。在巴黎和会上,寡言的日本代表提出了三个议案——关于山东权益、关于南洋诸岛以及废除种族歧视法案,后两条特别是最后一条,据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广部泉的研究,恰是列强与日本妥协的一个原因所在。第三部最精彩的莫过于一个小人物“王先生”(伯衡),他向《纽约时报》投书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引来了一番论战。以公共史学为写作旨归的王笛,在此发挥了职业史家考索探幽的本领。
第四部三章讲中国的觉醒。巴黎和会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会议期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王笛称之为“巨人醒来”。确实如此,五四运动从命名到赋予其意义都体现了自我规定的主体性。在一般性的叙述之外,王笛发挥了微观史家的本领,挖掘出纽约《文摘》上报道的名为马骏的南开中学学生领袖的故事。马骏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倾向共产主义,后赴莫斯科接受培训,回国后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8年死难。这个鲜为人知的人物,诠释了五四后中国政治风向的转变以及一代为共产主义理想捐躯的知识青年的形象。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文化和思想上的冲击,美国专栏作家充满期待地称,“比胜利更伟大的是中国的觉醒”。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观察历史的多元视角
巴黎和会上中国落空的希望在下卷第五部有了新的展开。1922年2月,由美英主导的华盛顿会议签署了九国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日本交还山东主权和胶济铁路,自主地从汉口和山东半岛撤军。华盛顿会议没有巴黎和会上的紧张感,在素描了相关情景后,王笛回到“个”的视点,写美国报章上的报道,写在美华人和留学生的动向。第一章登场的司徒雷登和史迪威再次出现。此时的司徒雷登正在北京忙于筹建燕京大学,请来了著名设计家亨利·墨菲,后者设计了雅礼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20年9月,史迪威携家带口来到中国,作为语言教官的史迪威曾在山西修过路,目睹过日本人的跋扈。赛珍珠从华北到了江南,细心观察民间烟火,留下了一桩情杀记录。1921年赛珍珠的母亲在其老家——“镇江”去世,被埋葬于她经常经过的外国人墓地。晚年赛珍珠回忆起墓地三位不知姓名的水手墓碑上的碑文:As I am now, so must thou be; Therefore prepare to follow me(而今我先下黄泉,他日来此轮到你),这段话显然出自拉丁谚语——Tu fui, ego eris(我曾经是你,你将会是我)。
围绕山东胶东半岛的外交交涉结束不久,位于山东西南的临城一夜间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1923年5月5日,悍匪孙美瑶率众劫持了在津浦线上疾驶的列车,200名绑票中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商人和旅行家,是为“临城劫车案”。鲁西南位于数省交界之地,绑票撕票时有发生,因为关涉外国人,事件注定要和平解决,结果孙美瑶释放人质,所部被编入山东军阀的部队里。孙美瑶制造如此惊天大案,注定了其难以善终,案件平息半年后,人质鲍威尔获悉山东省长借故杀死了孙美瑶。临城劫车案让中国政治和社会暗黑面大白天下。费正清曾揶揄新闻记者如追逐被丢弃的吃剩罐头的苍蝇,美国记者在争先报道土匪的同时,也论及军阀。在直系、皖系、奉系军阀中,记者对直系吴佩孚充满善意,称之为中国的“强人”和“希望”,但是,中国依然是军阀各自为政,这种局面的打破要等自南而来的国民革命。
王笛很善于讲故事,在打打杀杀中适时插入弱势群体——女性的片段,一方是被卖的丫鬟,一方是女性参政的诉求,在这种充满张力的魔幻世界里,王笛以赛珍珠的笔端转述了一个年轻男佣和两个寡妇佣人的故事。赛珍珠的佣人李嫂软禁了男佣,在赛珍珠的撮合下二人虽然“结婚”,但男佣心念另一女佣;由于担心“丈夫”逃走,李嫂在一次争吵后又将其囚禁。赛珍珠责怪李嫂不该囚禁人,李嫂说:“他还想要另外一个女人——要我们俩”。赛珍珠答曰:“很多中国男人不都只有一个妻子!”李嫂坚定地回答:“不行”。闻后赛珍珠很是感慨,革命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一般民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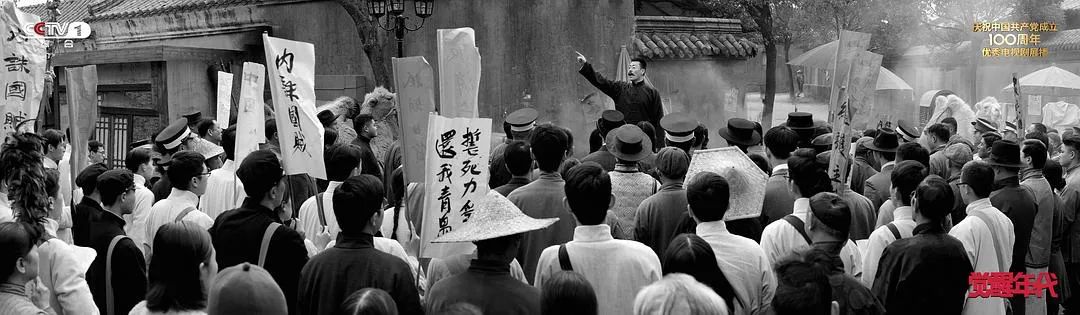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在政治的混沌中,新的可能性愈发明显——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在第七部四章中,王笛切换视角,观察革命兴起的不同面相。记者拉德利·托马斯、著名教育家保罗·孟禄等认为学生运动将是现代政治的重要资本,同时也含有一定的危险性。对于在苏俄支持下由国共合作开启的国民革命,王笛通过一个尚未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就加入《纽约时报》的特派记者——哈雷德·阿班的经历予以追踪:阿班在广州目睹了省港大罢工,在上海因轻度中风而九死一生,在北京办报受挫,邂逅北伐军,被日军逮捕,等等。来华军官史迪威已然成为有经验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岗哨报》上开辟专栏,发表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同情民生的艰辛,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前,即已预言张的前途黯然。定居南京的赛珍珠经历了北伐军到来时发生的事件,在日本避居了一段时间返回中国后,赛珍珠曾在上海短暂逗留,华洋两重天的生活令其感到厌恶;赛珍珠对国民党的革命冷眼相看,认为不过是“漂亮的旗号”。回到南京后,赛珍珠目睹了国民政府因欧洲某王子来访,为了“遮住这古城中的龌龊的一面”而暴力拆迁的场面。
为何写史?如何写史?
如果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写作,本书应该就此打住,但是,王笛不忘作为职业史家的身份,在第八部用两章的篇幅前瞻后顾,反思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孤立主义的实际作用。虽然,半途而废的威尔逊主义令中国大为失望,虽然总想着改变中国的美国未能如愿,但正如王笛所说,“既然美国来过中国,就会留下它的痕迹”,而且这痕迹还在延续。1923年1月24日,芮恩施在上海英年早逝。珍珠港事件后,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记者鲍威尔被日军囚禁,这位临城劫车案的人质在狱中因坏疽病而失去了双腿,曾谓:“与日本侵略者相比,我们更喜欢中国土匪”。在中缅战场上扬威的史迪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即时报道西安事变的阿班,都是王笛描述的对象。在本书第一章第一个登场的司徒雷登,被定格在本书最后一章的最后——“别了,司徒雷登”。
以上是我阅读本书随手记下的杂感。在享受了久违的阅读愉悦后,一个朴素的问题油然而生:为何写史?一位19世纪的哲人批评同时代学人俨如频繁下蛋的母鸡,叫的次数很多,所下蛋的个头却很小。目下坊间的很多书籍也有这一特点。一些作者为写而写,犹如一些赌徒之所以赌博不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继续玩,待在机器的迷境里,停留在风暴眼中。在AI时代,我们生活的印刷文化的黄昏业已来临,重新思考为何写史?如何写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不消说,写史的目的首先在追求“真实”。事实有两个层次:实在的和表象的。实在的事实是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本书的他者——美国人耳闻目睹的事实是表象的事实,受到当事人的视点、职业、意识形态等制约。王笛在前言引用费正清的话作为题头语颇具深意:“长期以来,美国试图让中国变得更像自己。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尝试尽管屡屡失败,却仍然锲而不舍地努力”。这是战后美国人在总结美国为什么失去中国而得出的一个结论。但是,在充满变数的历史过程中,历史的结论未必是历史演进的主格调,也未必是执拗的低音。他者表象的事实可一分为二,一为被证明是客观的正确的,一为被证明是主观的有误的,二者中我更属意后者,不仅因为正是后者的不断叠加导致了费正清所说的结果,更因为后者包含了当事人自以为是的主观判断。如凯蒂女士对中国妇女在新时代已有的和将有的作用所做的满怀激情的演讲——“因为她们的积极参与,清政府才被推翻,共和才能建立。现在她们要求选举权,否则她们将使用武力”。这种带有对未来期待的事实含有当事人对所见之事的价值追求,蕴藉了观察者的主观期待,涉及到追求真实的目的为何之问题。
“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回答幼子历史有何用时给出的一个回答是记录。历史(事件)有如恒河沙数,记录绝非漫无目的,有着强烈的主观动机——通过价值判断而追求真理。王笛这部著作完成于多年前,阅读之下,令人会心一笑,仿佛是为“讲好美国故事”而赶出来的急就章。确实,美国的官员、记者、商人、军人、学者、旅行者等普遍对中国表达了友好、同情和期待,这与同时代的日本截然相反。五四时期,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举办过一次讲演会,经营药品生意的内山完造对主讲人说,在重庆江边曾目睹两位中国壮汉与要回国的瑞典牧师告别时嚎啕大哭的情景,认为牧师一定为当地人做了很多善事,而日本人在中国一味地追求私利。1922-1928年法国驻日本外交官、诗人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在信函中指出,日本正陷入自说自话的孤独的帝国主义境地。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如果仅止于真实和真理,历史书写这一行为就可以完全归入科学了,正如马克·布洛赫对何为历史给出的另一个回答——美感——所表征的,历史书写是有伦理指向的,真正打动人心的著作不只在文字修辞上,更需要写者与被写者之间心灵的碰撞——真情。王笛的叙事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均有精巧的安排,绝不放过细节和微声。前述赛珍珠回到南京后,看着南京国民政府忙于粉饰大街小巷,感叹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是多么为他们深爱着的国民感到羞愧,而这种羞愧又是多么动人而可怜啊!”这句看似平淡的摘译,读后令人浑身震颤。
读罢本书,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另一个问题是,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换言之,如何在当下的历史书写中给本书定位?《中国记事》是一本独特的断代史。所谓“独特”是指本书是以他者的眼光来看中国历史,与通常以中国人的叙述为主要资料的历史著述很不相同。从本书的铺陈看,他者眼中的中国历史未必不客观,与中国人讲述的历史未必截然二分,这说明当时的美国人的中国认识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有交错的,更根本的是,历史叙述具有基于人的同一性而来的普遍性特征。缘此,我强烈推荐习惯于同质化历史的读者阅读本书。即使从获取知识的角度而言,打开本书也能得到难得的新知,如1915年的《二十一条》是何时消失的?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
与一般的通史著作不同,《中国记事》言必有出处;与一般的专著别异,为了阅读方便,《中国记事》没有繁琐的征引,阅读之下,颇有非虚构写作的感觉。伴随历史作为“消费品”需求的增大,时下非虚构写作颇为盛行。我在多处讲过,非虚构写作绝不是历史和小说之和,也绝非把事件写成动人的故事。非虚构写作是基于有限的证据和合理的推论而来的知的冒险,在历史的空白处宣示主权。在此意义上,《中国记事》颇有正本清源的示范作用。
我在阅读本书过程中,不时闪过从日本角度写一部《中国记事》的冲动,由于日本及来华日本人与这段历史的深度关联,可写的内容很多。但是,我又很快不断打消这一念头,因为与王笛这种农耕型学者相比,我属于游牧型,既没有他的定力,更主要的是我从本书中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知的刺激,应该接着作者的探索继续走下去。王笛的文字不激不随,不麻不辣,于静静的阅读中可品出既麻又辣的滋味,有道是文若其人。
作者/孙江
编辑/刘亚光
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