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为什么还能撑三十年?暨《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读者见面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一书作者成长,文史作家、书评人张向荣,作家、学者李天飞围绕“后诸葛亮时代”的三国政治、军事、外交以及历史非虚构写作的文学价值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对谈。

“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为什么还能撑三十年?暨《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读者见面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从234年至蜀汉灭亡的263年,是蜀汉整整三十年的“后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作为三国之中最弱小的国家,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一书中,成长将目光聚焦于蜀汉建兴十二年(即公元234年,也是诸葛亮去世这一年)之后的三国。从这一年开始,三国褪去了英雄的光芒,呈现出历史真正的底色。魏、蜀、吴三国经历开国一代的筚路蓝缕后,开始面临各自的困境,如:立国的正统性、权力代际的过渡、君主与权臣的龃龉、军事战略的转变、功勋子弟的崛起、边境民族矛盾的激化等。将它们放在三个政权彼此之间的冲突、联盟、制衡的复杂关系中,则又凸显出特别的意义。
为什么选择三国的最后三十年作为叙写对象?面对这一提问,成长表示,“很多读者对三国历史的印象都来自《三国演义》,但《三国演义》忽略了三国后期的很多重大事件,如费祎遇刺、诸葛恪北伐等,这些事件对当时的政治局势都有很大影响。”因此,成长希望《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能够呈现魏、季汉、吴在最后三十年中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真实历史格局。他解释说,使用“季汉”的称呼是对历史本源的遵从,刘备继承两汉正统,以“汉”为国号,“蜀”只是入晋之后对割据一隅的政权的蔑称。作为今天的历史写作者,有必要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
在回答“是否存在历史必然”的问题时,成长认为:“最让我感到遗憾的人物是邓艾和魏延。邓艾至少有事功,而魏延在《三国演义》里的被丑化,其实是源于他与诸葛亮的路线斗争,子午谷之谋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当然,这种策略的作用主要是对敌的震慑力。”李天飞则表示,自己在三国里最大的“意难平”是曹髦。他的抗争不仅是皇权与相权的抗争,也是为个人尊严的抗争。张向荣认为,何晏和夏侯玄都曾是曹爽最重要的谋士,是正始年间主要的执政者,但由于他们在高平陵之变后先后被杀,相关史料大多被删改,已经很难看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此两人还是玄学形成时期的关键人物,如果他们没有死,玄学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番面貌。三位嘉宾还分享了与三国有关的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等。
以下内容节选自《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之《武侯的子孙》,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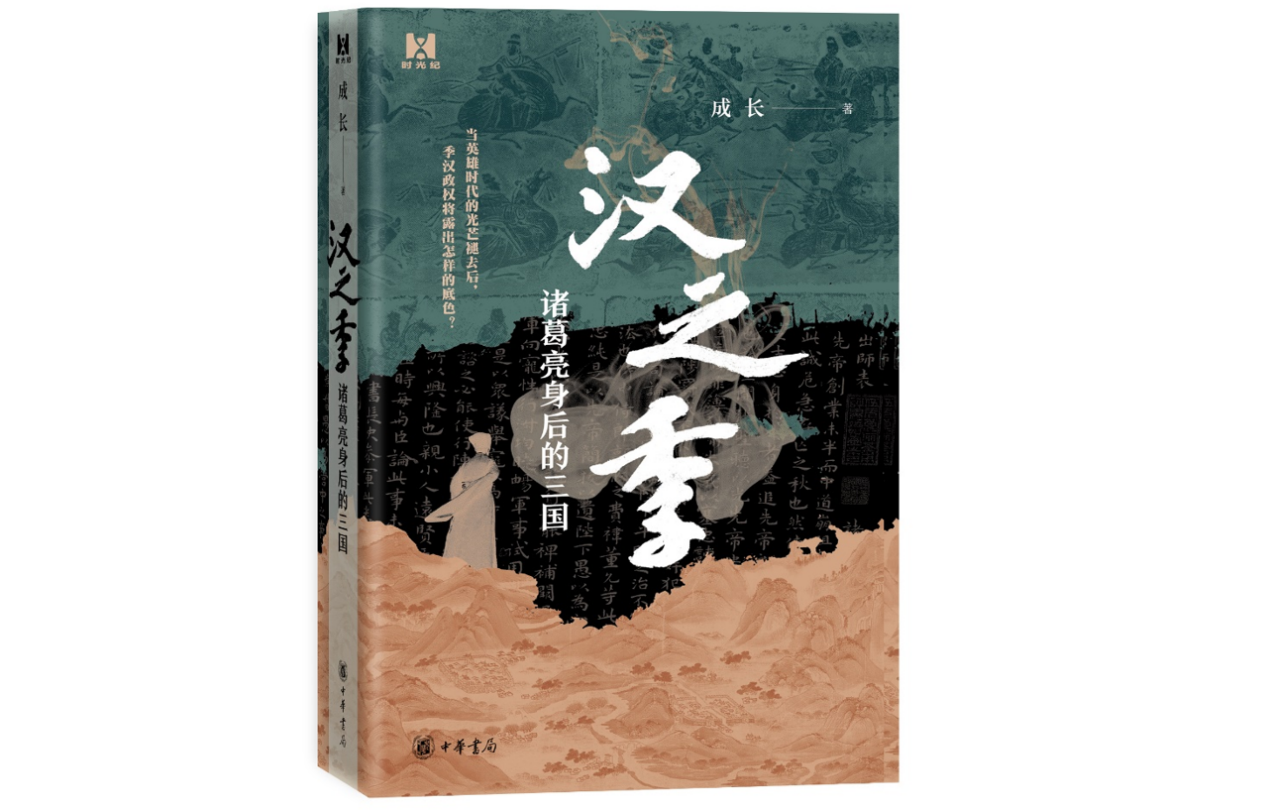
《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成长 著,中华书局2025年4月版。
顶着武侯光环的诸葛瞻
蜀水,一支匆忙组建而成的军队从成都出发,奔赴涪县前线。如果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是后人对季汉人才匮乏的嘲讽,那么这支部队的将帅们更适合为这一悲哀的现实做注脚——他们是清一色的季汉功臣后裔:诸葛亮之子、卫将军诸葛瞻,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张飞之孙、尚书张遵,黄权之子、尚书郎黄崇,李恢之侄、羽林右部督李球。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战场。
季汉原本是有功臣子弟上前线的传统的。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曾给东吴的兄长诸葛瑾写信云:“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信中他解释了没有将诸葛乔留在成都的原因——季汉的所有将领子弟都要到前线负责物资运输,诸葛乔虽是诸葛亮的过继子也不能例外。不幸的是,诸葛乔不久就在北伐战事中死去。可能正因为这件事,让季汉朝廷对于功臣子弟的安全格外照顾,故而此后三十余年间,季汉军队虽征伐不断,但军中已经鲜少看见功臣子弟。

《三国》(2010)剧照。
从以下名单中我们大体能够看到,季汉功臣子弟几乎都在位于成都的尚书台、御史台、侍中寺等机构任职,即便是军职,也多是掌管禁中羽林、虎贲等宿卫兵:
关羽之子关兴:侍中、中监军
关羽之孙关统:虎贲中郎将
张飞之子张绍:侍中、尚书仆射
张飞之孙张遵:尚书
赵云之子赵统:虎贲中郎,督行领军
法正之子法邈:奉车都尉
麋竺之子麋威:虎贲中郎将
向朗之子向条:御史中丞
蒋琬之子蒋显:太子仆
费祎之子费承:黄门侍郎
邓芝之子邓良:尚书左选郎
诚然,吴、魏两国的贵戚子弟也有出任上述职位者,但相比而言,季汉的功勋子弟们在军事上的参与度明显更低。东吴受世袭领兵制的影响,从孙权晚期开始,其长江防线上的各戍镇督将就已陆续由“二代”接班,如柴桑督陆抗(陆逊之子)、西陵督步协(步骘之子)、乐乡督施绩(朱然之子)等。曹魏方面,勋贵后裔典兵为将者可谓不胜枚举,且不说曹丕、曹叡时期掌军的曹真、曹休、夏侯尚之辈,即便是司马氏秉政之后,仍有诸多开国功臣子弟活跃于对蜀、吴的前线战场上。如陈群之子陈泰、陈矫之子陈骞、胡遵之子胡奋等,更有如桓阶之子桓嘉、乐进之子乐綝殁于国事。而姜维北伐期间,有记载身在汉中、阴平等战争前线的季汉功臣子弟唯有护军蒋斌、牙门将赵广、参军来忠(来敏之子)三人。
季汉的北伐如火如荼,但擎大旗的却是“羁旅托国”的姜维,那些衔着金汤匙长大的功臣子弟袭着父辈的爵位,领着丰厚的俸禄,躲在安逸的成都城内,仿佛这一切都与自己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令人心寒的现实。季汉将他们保护得太好了,他们既缺乏战争的淬炼,更丧失了父辈的胆识与勇略,这使得他们之中难以出现如陈泰、陆抗那样卓越的军事人才。整个国家不得不对姜维更加倚重乃至产生过度的依赖。如今,在姜维分身乏术时,顶着武侯光环的诸葛瞻终于肩负起了武侯的责任,他那卫将军的职位,也终于在他统兵卫国的那一刻变得名副其实。
“进屯绵竹,埋人脚而战”
诸葛亮去世的时候,诸葛瞻只有八岁,他给父亲留下了“聪慧可爱”的印象,而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抽象的身影。他只能在未来成长历程中通过他人的描述在想象中构建父亲那伟岸的形象。诸葛瞻没能在自己最好的年岁里接受父亲的亲自教导,这让他与经历系统家教的司马师、司马昭、陆抗相比,存在着先天不足。他甚至不如钟会那样有一个好母亲。教育的缺失、国家的溺爱、民众的过誉让诸葛瞻逐渐滑向了诸葛亮生前担心的“不为重器”的境地。于是,当毫无统兵经验的诸葛瞻,带着一批同样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功臣子弟迎击在战火中浸淫半生的邓艾时,其结果早已注定了。
从江由戍南下汇入金牛道,魏军想要抵达成都,仍需攻破三重门户——涪县、绵竹、雒城,这也正是当年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取益州的老路。诸葛瞻抢在邓艾之前督诸军抵达涪县,然而他停驻在此,盘桓不敢进攻,充分暴露出一个初学者的生疏与手足无措。军中唯一懂点用兵之道的是黄崇——大概是因为他的父亲黄权降魏,使得他在子弟中低人一等,故而格外勤学苦读——黄崇见涪县处于一片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就建议诸葛瞻趁邓艾还没有走出山地之时,抢先派兵占据险要之地进行阻击,让敌军无法进入平原地区。这是经王平在兴势之战中验证过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可诸葛瞻缺乏胆识,不敢主动进军,对黄崇的献策不予采纳,急得黄崇连眼泪都流了下来。结果,错失先机的汉军,眼睁睁地看着魏人顺涪水而入平原,汉军前锋甫一交锋,即被攻破。诸葛瞻不得不放弃涪县,退守绵竹。
绵竹属广汉郡,当年李严、费观就是在这里向刘备倒戈而降。邓艾兵进绵竹,给诸葛瞻送去一封劝降信,许诺他如果归降,就会表奏他为琅琊王。诸葛氏本出琅琊,许封琅琊王有爵封本籍、光耀门楣之意。当时司马昭尚未称王,邓艾开出如此离谱的条件,诸葛瞻自然是不可能信的。他怒斩邓艾使者,勒兵列阵要与邓艾一决胜负。这一下,诸葛瞻就中了邓艾的圈套。邓艾送劝降信的目的根本不是要诸葛瞻投降,而是激怒诸葛瞻放弃坚守城池,与魏军野战。故而何焯对诸葛瞻的用兵大为不解,说:“艾军入死地,理无反顾。而瞻不知凭城持重,何哉?”其实,也无需如此惊讶,诸葛瞻缺乏基本的用兵经验,突然担负起这样的重任,最易感情用事,与邓艾这种沙场老将对垒,他在心理战中就先输了。
邓艾将士兵分为左右两路,分别由师纂和邓忠统帅冲击汉军。野战本是魏军强项,但邓艾军士一路跋山涉水,疲于赶路,战力已经大为削弱,而汉军又有主场作战的优势。一战下来,邓忠、师纂败退回营,灰心丧气地说:“敌人还不可攻击(“贼未可击”)。”邓艾拍案大怒,说:“现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刻,胜败就在此一举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甚至要将两人推出斩首。邓艾倒是想杀了司马昭安插在自己身边的这个碍眼的师纂,但他当然不会杀自己的儿子,这不过是激将法。此举果然有效,邓忠、师纂连忙请命再战,一场血战过后,汉军大败,诸葛瞻、诸葛尚、张遵、黄崇、李球皆在此役中殉国。
据唐人《元和郡县图志》载,诸葛瞻见兵败如山倒,叹息道:“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目而反?”于是“进屯绵竹,埋人脚而战”,最终父子战死。“埋人脚而战”,应是类似死不旋踵、誓不后退的作战方式,足见当时汉军作战之壮烈。
诸葛瞻所言“三罪”,既仇恨黄皓,也憎恶姜维,这显示出季汉末期朝中局势的复杂性。作为诸葛亮的儿子、荆楚新贵的核心人物,诸葛瞻不可能不想继承父亲的遗志,让季汉重振雄风。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困、朝政废弛的国家,即便他和他的盟友董厥、樊建取得了尚书台的掌控权,也依然无法施展拳脚有一番作为。阻碍诸葛瞻施政的,正是代表宫中权力的黄皓和代表军中权力的姜维,因此,尽管黄皓和姜维水火不容,他们在诸葛瞻眼中却是同样将国家拖入泥淖的人,是他的敌人,是季汉的“罪人”。
他选择在绵竹战死疆场
可见,诸葛瞻到死都没有走出父亲的阴影,他始终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诸葛亮事业、权力、地位的唯一继承者,在众人的赞美声中,他从不觉得自己德不配位,直到绵竹的惨败才让他猛然惊醒,但为时已晚。他选择在绵竹战死疆场,固然有忠肝义胆的情怀,但更多的可能是——他无法背负起败军的责任,更无法容忍季汉士民对他的批评和失望,只有一死才能掩盖住他在国家危难之际的平庸无能。但恰恰是这一死,凸显了他性格上的脆弱和怯懦。在季汉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赴死而为自己博得一个忠烈的虚名是容易的,而为了国家的存活苟全性命,以至于因此而遭受谤毁反而是最难的。诸葛瞻选择了前者,而姜维选择了后者,他们的人格与胆识之高下可谓立见。

《三国》(2010)剧照。
其实,诸葛瞻根本不必在这里去死。在他身后不远,就是成都最后一道门户雒城。当年刘璋之子刘循率众守雒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抵御刘备长达一年,其间还射杀了刘备的军师中郎将庞统,让刘备陷入极大的困境。以雒城的坚固,加以布防,足以抵挡住邓艾的攻势。而此时邓艾深入蜀地,已成为一支孤军,若能将他拖在雒城之下,等姜维、阎宇任一路援兵到来内外合击之,未尝不能扭转局势、绝处逢生。诸葛瞻决定在绵竹赴死,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责任,罔顾国家的安危,这与街亭战场上弃军而逃的马谡又有什么区别呢?
被诸葛瞻拖累的不仅是季汉的将士,还有他年轻的儿子诸葛尚。诸葛瞻阵亡时年仅三十七岁,诸葛尚顶大不过十六七岁。《华阳国志》载,诸葛尚见大势已去,也留下一句话:“父子荷恩,不早斩黄皓,以致败国殄民,用生何为!”然后驱马赴魏军而死。诸葛尚只憎恶黄皓,没有忌恨姜维,说明他比他的父亲更清醒一些,知道季汉的根本问题还是出在朝堂之上、宫墙之内。他感叹“父子荷恩”而致倾败,实际上是在委婉地批评他的父亲没有匡正刘禅的得失,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宰辅。但如今说这些已没有意义,诸葛尚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让季汉的希望更加黯淡。
邓艾在绵竹击败诸葛瞻后,乘势南下雒城,成都已经咫尺可望。诸葛瞻父子的阵亡无疑加重了蜀中的恐慌气氛。“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朝堂之上更是乱成一锅粥,刘禅召集群臣商议了半晌,众人七嘴八舌,也没有什么好的应对之策。强敌来袭,无非战、守、走、降四策。但自诸葛瞻丧师败绩后,成都守军已所剩无多,且几无斗志可言,应对邓艾的虎狼之师无异于以卵击石。至于守城,成都已经近半个世纪没有经历战争了,这座自古以来就以富足、安逸、闲适著称的城市根本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且不说城墙是否坚固、士卒是否精壮、防御物资是否齐备,单是将城外的居民、粮谷、物资迁入城内这一件事,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这样下来,朝臣们的意见集中在了“走”字上。一部分人提出,汉吴两国为同盟关系,可以投奔吴国暂避锋芒。一部分人认为南中七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以前往避难。
正在此时,光禄大夫谯周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反驳了这两种观点。他说:自古以来就没有寄身他国的天子,如果投奔东吴,那就形同于做了东吴的臣子。而吴国弱于魏国,将来魏国灭掉吴国,我们就要受到第二次亡国之辱,那还不如一次受辱。至于南中,如果要去就得早做打算,现在敌人兵临城下,士卒人心惶惶,不能信任,恐怕还没等出发,就发生了不测(大概指兵变、溃散之类),根本到不了南中。至此,谯周终于当众亮明了自己的主张——开城投降。
整合/何安安
原文作者/成长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