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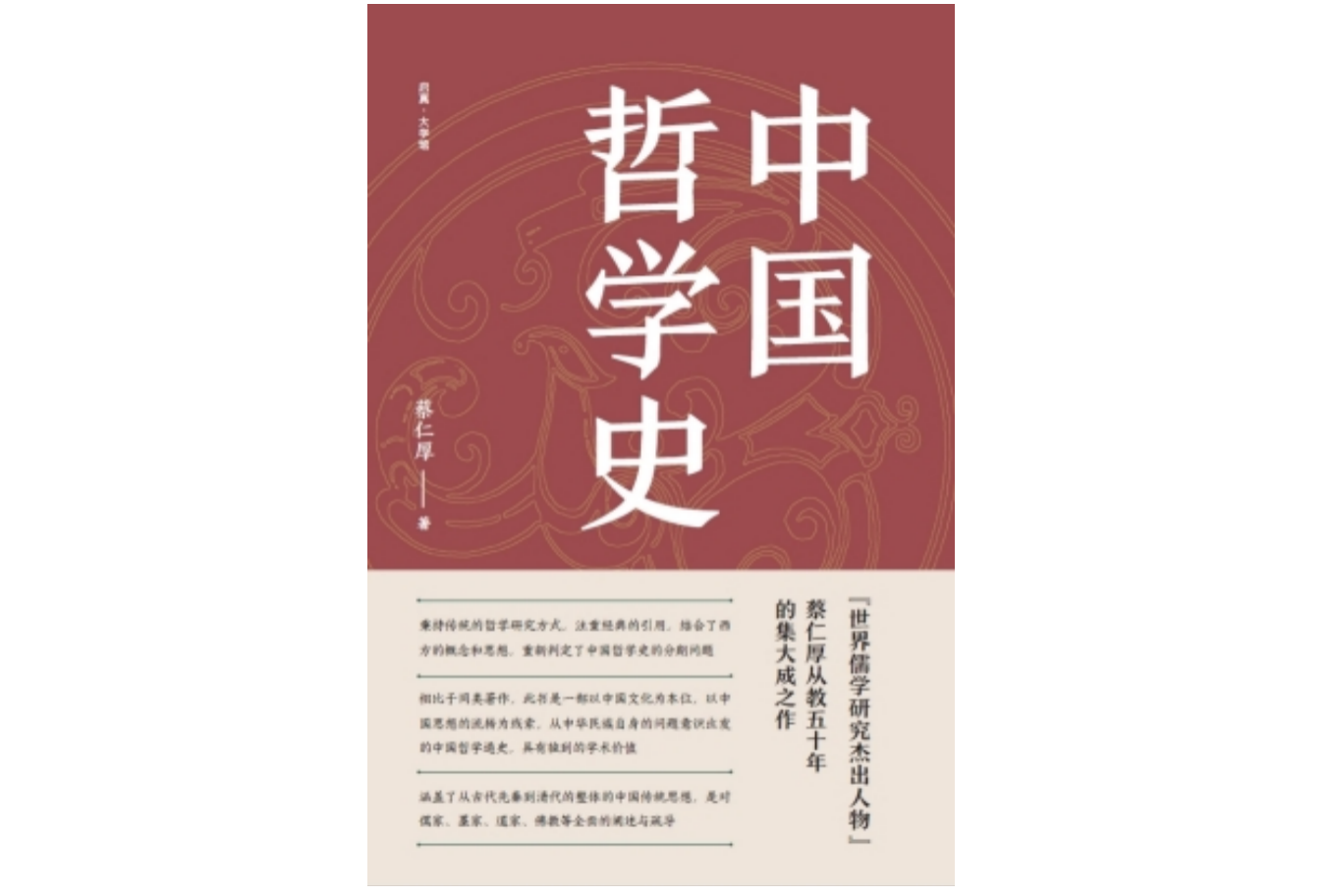
《中国哲学史》,蔡仁厚 著,启真馆丨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版。
对中国来说,“哲学”乃是20世纪的新词。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容纲领和学科分类,早已形成规格。譬如“经史子集”,“经”有章句与义理之分,“史”有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之别,“子”又分为诸子百家,“集”则人各一部,包罗尤其驳杂。但中国学问,总是以“生命”(人、人生、人事)为中心,不同于以“知识”为中心的西方之学。近百年来,西方文明挟其强劲之势不断冲击东方,中国文化招架不住,于是国人只好自居落后,奉西方为先进。单单哲学史这个部分,便使中国“倒架子”了。
20世纪前半叶,有两本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一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书只写到先秦阶段,我们无从知晓它全部的内容。现在只能就其书“以老子开头”这一点加以探讨。胡适说老子是“革命家”,是“时势的反动”。然则老子这个反对派,他反对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老子反对“圣、智、仁、义”(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那么,“圣、智、仁、义”算不算是一个价值系统中的价值标准呢?
如果算,它是谁创立的?它有没有产生过正面的作用呢?
一个能起作用的价值系统,是否也含有一种哲学思想呢?
如果不能否认它也含有一种哲学思想,那么为什么加以割截而不予理会呢?
也许有人说,胡适书中列有“诗人时代”一节以代表老子以前的思潮,但胡适所叙述的其实不是什么思潮,而只是引用《诗经》里不满社会状况和现实政治的诗句,以表现诗人们怨怒的情绪而已。依胡适书中的叙述,似乎中国的历史文化,一开始便是黑暗混乱,一无是处。在此,我们不禁要问:《诗经》里面是否也有从正面表述清平政治的诗篇呢?是否也有赞颂先王功业和圣贤德教的诗篇呢?事实上当然有,而且还不在少数。然则,胡适何以一句都不提呢?而且,《老子》以前的文献,也不只是一部《诗经》,《尚书》里面也有哲学性的观念,为什么一概加以抹杀呢?
一本哲学史,对于这个文化系统“创始阶段”的思想观念,不做一字一句的正面说明,而开天辟地的第一个哲学家竟然就是“反对派”。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不及格的写法。冯友兰的哲学史倒改向正面论述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先讲孔子,而且对孔子以前有关“宗教的、哲学的”思想,也有所说明。不过,冯友兰的哲学史,却有更大的问题。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史极其简单地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

《孔子》(2010)剧照。
他如此分期所显示的意思,主要有三点。其一,他以西方哲学史的分期模式来划分中国哲学史的阶段。其二,他以汉代以前为“子学时代”,这是民国以来一般的说法(其实并非妥当,因为诸子之前还有上古三代),以西汉董仲舒一直到清末为“经学时代”,则是冯友兰个人的判断。他认为西汉以来各个阶段的哲学思想所表现的精神都是中古的,相当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其三,基于以上的判断,他颟顸地认为,中国哲学史没有“近代”。
西方文艺复兴开启的是一种“反中古”的精神方向。从哲学方面来说,就是不愿意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而要求恢复希腊传统中哲学独立的地位。在中国,宋明理学也自觉地要求恢复先秦儒家的慧命,以重新显立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位性。相较西方来说,宋明儒者“不满意两汉经生之学,不满意魏晋的玄学清谈,不满意佛教执中国思想界之牛耳”这种精神方向正与西方近代哲学“反中古”的精神相类似,怎么反而说宋明儒者的精神是中古的?而胡适认为的宋代以来的儒学是中国的“近代哲学”这一点,倒显示出他对历史文化的通识。
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进程为标准,妄判中国哲学史没有近代,正所谓“只知有西,不知有东”,不免有“出主入奴”之嫌。我们不可忘记,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无论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刻,还是生命情调、生活方式等,都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原创性、独立性)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问题和思想问题,有自己的文化生命所透显的原则和方向。因此,只能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没有出现西方式的近代哲学,而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近代阶段。中国哲学的近代,为什么一定要以西方哲学史的近代为模式呢?(至于说近代西方哲学很有价值,值得借鉴学习,则是另一个问题。前者是中国哲学的路向问题,必须另说另讲)冯友兰颟顸地认为中国哲学在自西汉以降两千年中所表现的精神都是中古的,拿来和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神学)等量齐观,这就表示他对中国文化生命开合发展的脉动根本没有感受,对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和哲学器识也欠缺相应的了解。
另外,在文献运用上,冯友兰也有“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例如他根据托名南岳慧思的《大乘止观法门》讲天台宗。陈寅恪的审查报告已指出此书为伪托。但冯友兰似乎不服善,仍然用这本与天台开宗的智者大师不相干,又不合天台教义的伪托之书来讲天台宗的思想。这样,就显得基本的知识真诚也有所不足了。
冯友兰的书比较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名家的讲述。他对惠施、公孙龙乃至荀子《正名》所做的疏解,都可看作他的贡献。不过名学并非中国哲学的重点,我们不能通过名学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至于中国哲学的主流,冯友兰的讲述则大体不恰当、不中肯。(譬如他说“良知”是一个“假设”,便是显例)
但冯友兰的书写于全面抗战之前,在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的反省、疏解还不够深入,对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三个阶段的学术思想,也还没有充分、明澈的了解。所以,冯友兰的哲学史写得不够中肯、不够恰当,并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是那个时代的客观限制。
为何还没有一部很好的《中国哲学史》?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很好的《中国哲学史》,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国人对文化传统的了解非常不够。不了解儒家、道家、佛教的义理系统,不了解三教学术的流变演进,如何能讲“中国哲学史”?
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港台地区及海外新儒家学者的研究却有了空前的发展。他们对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哲学思想,也已做了通贯的讲述。其中牟先生的贡献,尤其明显。
他以《才性与玄理》表述魏晋阶段的玄学,与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相比,此书进行了更深切而完整的讨论,可算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而文字之美,也超乎读者想象。对南北朝隋唐阶段的佛教,则以《佛性与般若》上下两册做了通透的讲述。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也是一部好书,但那是佛教史的角度,重在考订,又只写前半段。因此,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来看,魏晋玄学之后至宋明理学之前,这六百年间中国哲学思想的活动,仍然是荒芜地带。而牟先生此书,正是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讲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发展,对中国消化吸收佛教之过程及其意义,皆做了极其深入而恰当的诠释。

《孔子》(2010)剧照。
至于宋明阶段的儒学,则以《心体与性体》进行全面的疏导。依牟先生之观点,北宋前三家——濂溪、横渠、明道为一组,此时未分系,到伊川而有义理之转向。此下,伊川朱子为一系(心性为二),象山阳明为一系(心性是一),五峰蕺山为一系(以心著性)。而当“性”为“心”形著之后,心性也融而为一。故到究极处,象山阳明系与五峰蕺山系仍可合为一大系。此合成之大系,远绍《论语》《孟子》《中庸》《易传》,近承北宋前三家,故为宋明儒学之正宗。至于合成之大系(纵贯系统)如何与伊川朱子系(横摄系统)相融通,则是另一问题。于此,我们只能说,这三系都是在道德意识之下,以“心体”与“性体”为主题而完成的“内圣成德之学”的大系统。
牟先生讲述儒、释、道三教的三部大著,无论体系纲维的确立、思想脉络的疏解,还是义理分际的厘清,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精透和明澈。魏晋清楚了,先秦道家之学亦随之而清楚。宋明清楚了,先秦儒家之学也随之而清楚。再加上他的《名家与荀子》,又疏解了先秦的名学。于是,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史,乃能真得其终始条理,而可以做到恰当的讲述和诠释。
上面所说牟先生的三部书,等于是中国哲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三个阶段的断代史。而唐君毅的大书《中国哲学原论》(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则属于中国哲学的专题史。唐君毅所著各书,最具通识。他和牟先生是当代学人中对弘扬中国哲学贡献最大的两位。两人著书的撰写方式及其着重点,不尽相同。牟先生以透显义理的骨干和思想的架构为主,比较着重同中见其异,以使中国学问的义理纲维和思想系统得以厘清、确定。这是一种讲哲学系统和哲学史的态度。唐君毅的书,则以通观思想的承接与流衍为主,重在异中见其同,借此通畅文化慧命之相续,以显示承前启后的文化生命之大流。这是一种重视哲学思想之交相辉映和相续流衍的立场。
同时,两位学者还有一项成果,也是空前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做了比天台、华严更为深广的判教(台严判教,只及于佛教内部)。牟先生采取较精约而集中的方式,就人类文化心灵最高表现的几个大教来阐述。此可参阅他的《佛性与般若》《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三本书。唐君毅则通观文化心灵活动的全部内容,以剖析人类文化中各种学问知识、学术思想以及几个大教所开显的心灵境界。这是一种广度的批判,在人类哲学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另外,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虽然标为《先秦篇》,其实并不只是单属断代史,也是专题哲学史。这部书很有特色,对青年影响颇大。至于其三大册的《两汉思想史》则是通论周秦政治社会结构和两汉思想的功力深厚之作。
何以会有中国有没有哲学的疑问?
自从20世纪“哲学”一词进入中国,便引发了中国有没有哲学的疑问。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有儒释道三教系统,何以会有中国有没有哲学的疑问?此无他,以西方哲学为标准,鄙视中国自己之传统耳。此乃一时之陋识,勿足深怪。如今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学”与“思”,中国人终于可以就中西哲学的特质,提出正确恰当的对比;就中国哲学的精神取向,提出简明扼要的说明;就中国哲学之现代化与世界化,提出中肯的省思。同时,中国人已有了识见能力,可以厘清“中国哲学演进发展的思想脉络”,可以剖析“中国哲学异同分合的义理系统”,可以阐释“中国哲学的基本旨趣及其价值”,而且也能够衡定“中西哲学融摄会通的义理规路”。
因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世纪境遇,是前古未有的复杂和艰难,所以对于哲学的省察,不但要有慧识、睿见,而且还要有学力(质的意义上之学养)。否则,他的省察便只是一些浮泛的意见而已。自五四以来,真正致力于中国哲学之反省,真能为中国文化之新生贯注精诚而殚精竭虑的,还是当代新儒家的前辈学者。从梁漱溟、熊十力到唐君毅,都有极大的贡献,而牟先生更通贯地做了专门的省察和疏导,即《中国哲学十九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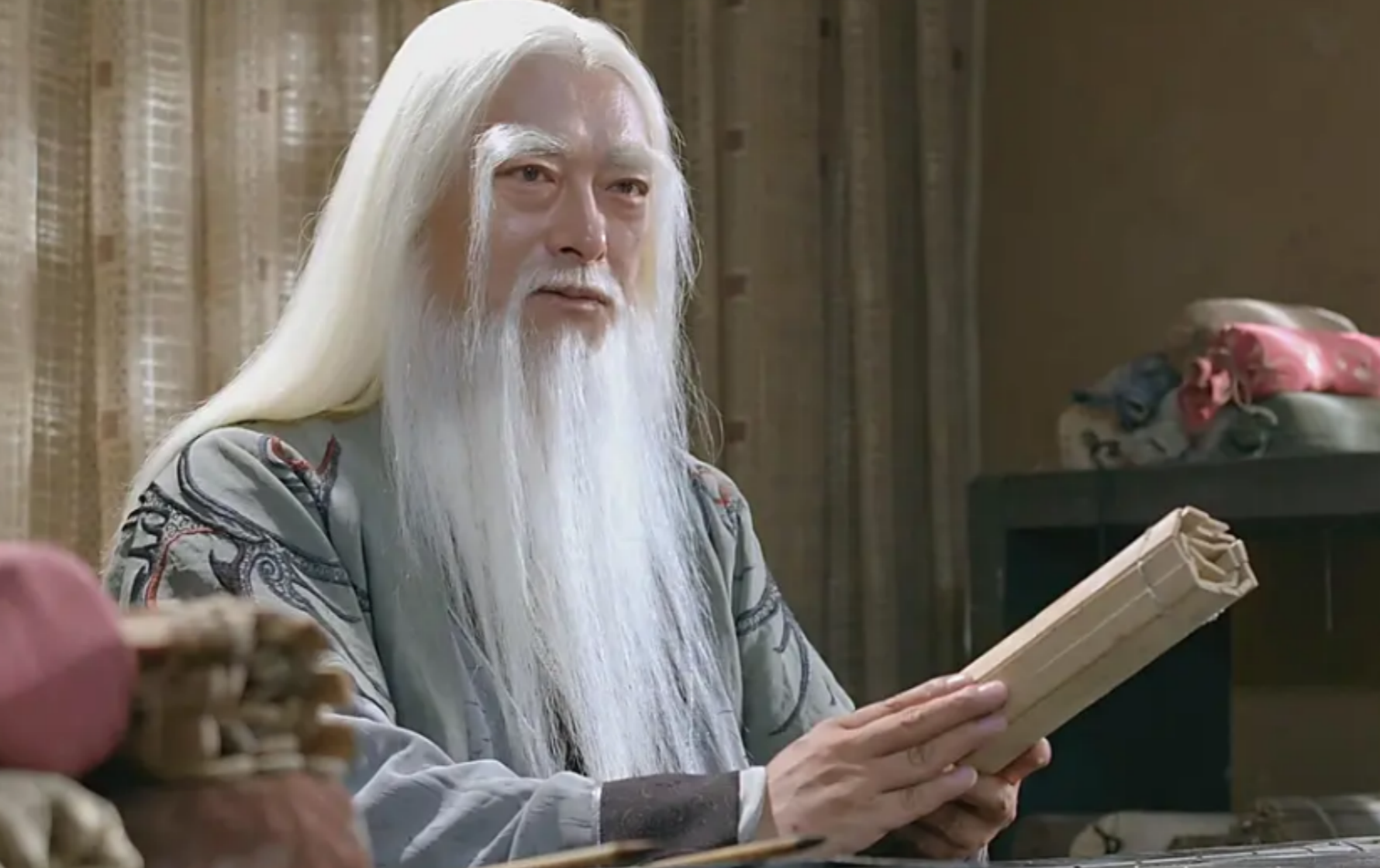
《老子传奇》(2016)剧照。
中国哲学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儒、道、佛三方面。然而此一东方传统,自明亡以后,久已衰微,尤其近百年来遭受西方文化之冲击,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哲学的精神面貌,乃渐模糊,甚至业已遗忘。牟先生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讲述中国哲学所蕴含的问题,并不是一时之间的兴会,也不是偶发的议论,而是切切关于中国哲学之系统纲维与义理宗趣者。其中厘定的各种问题,皆有所本。通过这一通贯性的综述,各期思想的内在义理可得而明,而其所启发的问题也意旨确切而昭然若揭。于是,固有义理的性格,未来发展的规辙,也确定了指标而有所持循。到此方知,文化慧命之相续不已,固可具体落实,并非徒托空言。而一部像样的、好的《中国哲学史》之写成,已经是可能的了。
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意旨,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如何通过现代语言,把中国哲学的思想阐述出来,把中国哲学的智慧显发出来,使它能为现代人所了解,而进入人的生命心灵之中,以表现它“本所蕴涵”的活泼的功能和作用。第二,如何对中国哲学做批判的反省,既要重新认识、发挥它的优点和长处,也要补救它的短缺和不足,以求进一步的充实、发展。这才是中国哲学现代化最积极的意义。
因此,中国哲学是否有前途,其决定的因素有二:一是中国哲学本身的义理纲维,能否重新显现出来;二是中华民族能不能如同当初消化佛教那样消化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在牟先生八十大寿时,他说,从大学读书以来,他六十年中只做了一件事,即“反省中国的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他认为民国以来的学风很不健康,卑陋、浮嚣,兼而有之。所以,有志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必须依据文献以辟误解、正曲说,讲明义理以立正见、显正解,畅通慧命以正方向、开坦途。
这三点确实是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讲哲学史,如果错用文献,便成大过差。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讲佛教天台宗时,不用天台开宗的智者大师的文献,反倒根据智者大师的师父南岳慧思的《大乘止观法门》来讲述天台宗的思想,而且经人(陈寅恪)指出,依然不改,实在很不应该。至于讲义理必须精透明确、恰当相应,乃是异同是非之所涉,更不可轻忽。而慧命的畅通,则是文化生命之“共慧”相续流衍的根本大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节选自《中国哲学史》绪论,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蔡仁厚
摘编/何也
编辑/王铭博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