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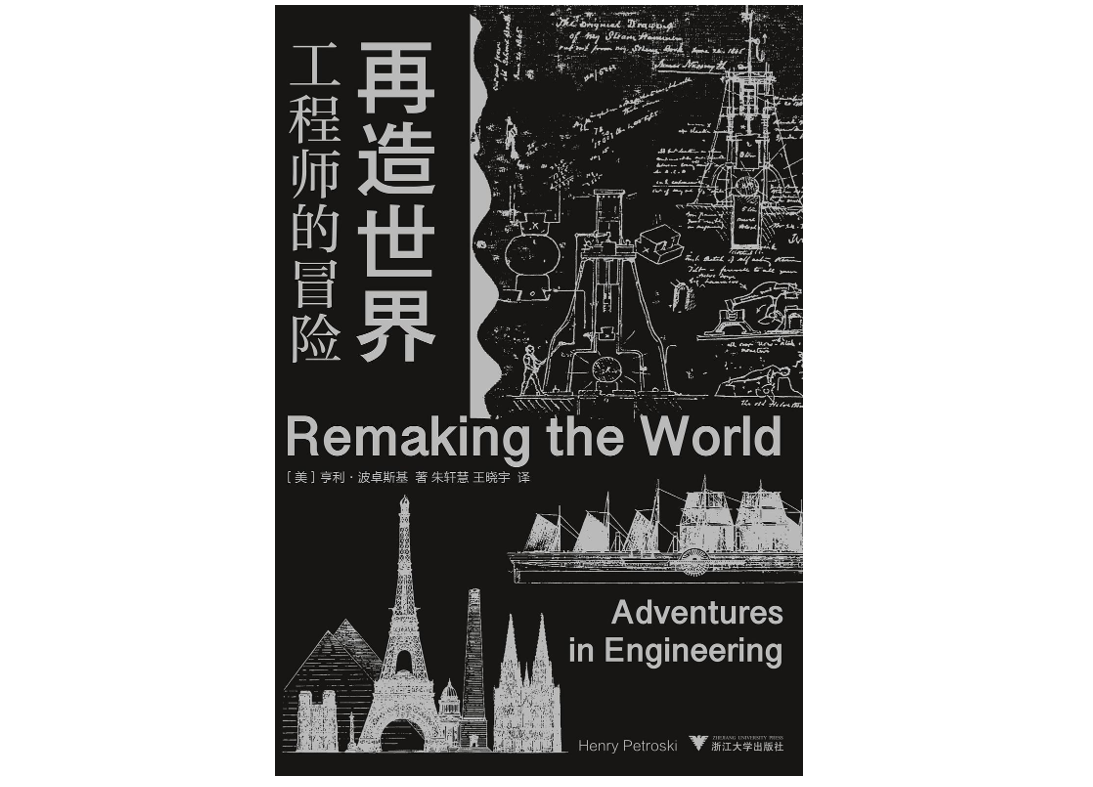
《再造世界:工程师的冒险》,[美]亨利·波卓斯基 著,朱轩慧 译,启真馆丨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版。
诺贝尔绝没有将工程学的成就排除在获奖范围外
诺贝尔奖源自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本人亲笔所写的遗嘱,原文还不到三百字。由于未经律师之手,这份遗嘱里没有寻常繁难的法律术语,即便是普通人,读起来也很轻松。在申明将财产中相对较少的部分留给自己的继承人之后,这位单身汉首先指定:
我名下所剩的全部可变现资产……应用于设立一份基金,每年以奖金的形式授予那些在此前一年里为全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
因此,诺贝尔的意图是很清晰的,设立这些奖项的目的是对成就给予充分的表彰。该奖项所认可的贡献似乎更接近工程和应用科学而非理论和基础科学,而且诺贝尔的主要意图应该是对技术产品的奖励至少要多于抽象的猜想和理论(如果不将其排除在外的话)。确实,基础科学家们所代表的基础科学的普遍看法是,尽管在未来可能产生一些没有预料到的实际后果,但他们的研究并非必须具有任何可以预见的或具有目的性的实际利益和物质利益。
在遗嘱的第二条,诺贝尔规定了奖金应来自可变现资产投资“安全证券”所得的利息,并这样分配:
奖金应该被分为……五等份,以此进行分配:每一等份分别颁发给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以及在促进各国友谊、废除或裁减军队和促进和平谈判上做出重要贡献的人。
诺贝尔似乎一点也不在意那些获得奖金的人是否具有专业资质或地位,也不在意其专业领域。很明显,对于他来说,那些发现或发明本身才是重要的,它们是出自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之手则无关紧要。“物理学”和“化学”这些术语只是为了区分应用的领域,而不是区分研究或专业分支的领域。
诺贝尔所处时代的物理学包含机械、热能、光学、电气、磁力的经典现象,以及在X射线和其他不可见射线方面取得的新发展。化学处理的当然是那些物理过程无法独立解释的现象。即使是在文学领域,诺贝尔似乎也明确了自己倾向于那些拥有超越自身目的的作品,或许可以将其称作“应用型文学”,一种如同约翰·加德纳所说的“道德小说”的叙事作品。由此可见,诺贝尔对于从艺术的角度评价艺术并不感兴趣,对于从科学的视角评价科学同样如此。

《诺贝尔的遗嘱》(2012)剧照。
在他的遗嘱中,诺贝尔明确了要由什么组织或团体来颁奖:
物理学奖与化学奖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学院授予,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授予,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出的五人委员会决定。
尽管世界公民诺贝尔曾生活在世界各地,但是他的家族却来自瑞典和挪威。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对于什么机构应该颁发奖项这件事他是否深思熟虑过,或者他只是在没有征求它们意见的情况下,随便指定了这些令他感到怀旧或只是看上去方便且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的机构。然而,从遗嘱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机构只能负责被指定奖项的授予,而不能规定奖项的范围类别。不幸的是,由于诺贝尔本人没有更严格地界定他想要颁发的奖项,因此是这些颁奖机构之后在事实上定义了这些奖项。
最后,这份遗嘱表明这些奖励应该是国际性的,正如诺贝尔的化学工程事业一样:
我明确希望,在确定这些奖励时,将完全不会考虑候选人的国籍问题,只有最值得的人才会获奖,无论他是不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
很明显,诺贝尔绝没有将工程学的成就排除在获奖范围外。实际上,遗嘱的第一条有关获奖人的规定并不关心他们是不是被认可的或正统意义上的科学家、作家或任何专家,而恰恰是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否值得被认可,因为他们“在此前一年里为全人类带来最大福祉”。
几乎在诺贝尔起草他的遗嘱七十年以前,作为土木工程师学会皇家宪章提案的一部分,托马斯·特雷德戈尔德提出了一种工程学的定义。尽管他使用的是“土木工程学”这一术语,但是这一定义此后被应用到所有非军事用途的工程学领域。依据特雷德戈尔德的定义,工程师们似乎正是诺贝尔奖的首要候选人:
土木工程学是引导自然界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所用以及提供便利的艺术,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状况和局面的那些最重要的自然哲学理论的实际应用。
以往的工程学与科技被囊括在“科学”之下
自然界的能量来源最终指向的当然是诺贝尔所处的19世纪的物理学和化学,自然哲学(如科学)的实际应用正是发明和发现的源头。确实,诺贝尔遗嘱中的用词几乎与特雷德戈尔德的定义一一呼应,“人类的福祉”等于“人类的便利”,并且诺贝尔对于奖项全球性的构想与特雷德戈尔德所认可的没有国家界限的工程学的目的十分相近。
显然,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中都有工程师参与,因此他们不应当首先从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中被排除。并且,在诺贝尔立下遗嘱的时代——也就是19世纪末——“科学”以及“科学的”这样的词相较于今天,更常用于表示工程学和对科学技术的探索研究。只需要读一读最近一期《科学美国人》上的《50年、100年和150年前》这篇文章,就能发现以往的工程学与科技是怎样全部被囊括在“科学”这个标题之下的。如果再看一眼1895年出版的《科学美国人》,这一点就更加确凿了。

爱因斯坦和斯泰因梅茨等人的集体照(《再造世界》插图)。
在诺贝尔写下遗嘱的那一年,《科学美国人》在封面上注明它是“一份关于实用信息、艺术、科学、机械、化学以及制造业的周刊”。具有代表性的封面绘画往往展示的是轮船制造、电缆维修船,或是其他新的工程学成就。一份典型的小报尺寸的十六页期刊会包含一整页发明目录,都是一周以来记录在案的被授予专利证书的发明。1895年《科学美国人》上的故事通常都是关于现在被归类为工程学或科技的内容。例如,在诺贝尔立下遗嘱的一周内刊发的一份《科学美国人》,有一篇关于曼哈顿银行着火案中火对于结构钢的影响的文章,里面包含了一张梁和桁架的工程纸。
用这本杂志当时的话来说:
每一期都包含十六页的实用信息以及大量新发明与新发现的原创版画,覆盖了工程学作品、蒸汽机械、最新发明、机械创新、制造产业、化学、电气、电报、摄影、建筑、农业、园艺及自然历史等领域。每周都有完整的专利列表。
我们所认为的属于科学和研究的内容大多被排除在外,收录在“一本单独的、不一样的出版物”中:
《科学美国人(副刊)》……涵盖了科学与实用艺术领域主要方向的杰出作者最近的论文,包含生物、地质、矿物、自然历史、地理、考古、航空、化学、电气、光学、热学、机械工程、海洋工程、摄影、科技、卫生工程、建筑、园艺、国内经济、传记及医药……
国内外最重要的工程项目、机械装置和产品的插图与介绍尽在《科学美国人(副刊)》。
可以看出,在诺贝尔的遗嘱起草并被翻译成英语的时代,“科学”和“工程学”两词的使用至少是交错混杂的。有两点是无可辩驳的:第一,工程学的成果确定无疑属于科学的范畴;第二,与专业机构相反,公众心中的工程学的地位至少与科学是旗鼓相当的。但到了颁发诺贝尔奖的时候,这些条件已经不再有利于工程学了。
工程师如何走入他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局?
工程学的角色并不总是像19世纪末期时那样。早在特雷德戈尔德被请去给工程学下定义的数个世纪以前,与科学相关的协会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说,在诺贝尔的时代以前,科学已经作为一门独立且拥有清晰定义的学科彻底实现了机构化。在牛顿那个时代,工程学不仅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而且在其他任何大学,显然都没有被认定是一门真正的学科,而当时的英国皇家协会已经十分繁荣了。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分门别类的工程学科是随着工业革命,从蒸汽引擎、钢铁桥梁和其他实体科技产品的建设和制造技艺中形成的。实际上,第一批现代工程师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应用科学,而是引领了科学。热力学可能被看作蒸汽引擎的实际应用,理论构造分析则被视作桥梁建造的应用。从手艺人对工具的巧思妙用中产生了科学现象,而科技随之而来的这一观点,具有说服力地反击了那种认为科技仅仅是应用科学的传统认知。
大约在19世纪中期,在工程师刚开始组建像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和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这样专业化的机构时;在工程学教育已经稳定发展但仍局限于技术学校,而与之相对的科学则在长期发展的大学中被教授和训练时;当随着诺贝尔也亲身参与的国际贸易日渐发展,工程和技术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关键因素时——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裂痕已经在慢慢变大。

《诺贝尔的遗嘱》(2012)剧照。
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第一届诺贝尔奖颁发时,科学已经对工程学产生了很大的敌意,而且不愿意放弃它有可能取得的任何利益。当时科学界的规模、特性和政治乃至职业优势,使得它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抓住诺贝尔的遗嘱所提供的机会,而技术界则无法做到。第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H.范特霍夫在他的获奖致辞中,一边谴责“技术成功的欢庆喧嚣淹没了自然法则轻柔的乐章”,一边对诺贝尔奖兼顾“纯粹”/理论科学和“实用”/应用学科的授奖表示认可。如果我们想理解事情是如何一步步由诺贝尔的遗嘱发展至此,而工程师又是如何走入他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局,就需要回溯一下遗嘱所表达的真实意图是如何被践行的。
科技这一研究领域产生的诺贝尔奖少之又少
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在1833年10月21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的父亲伊曼纽尔·诺贝尔是一位工程师兼发明家,小阿尔弗雷德正是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工程学,他们就像当时的很多父子一样。另外,就像那个年代许多既是发明家又是实业家的工程师一样,他的父亲破产了,迫使其全家在1842年从瑞典搬到了俄国。在这里,老诺贝尔获得了成功和名望,阿尔弗雷德的教育由私人家庭教师负责,他也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化学和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关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早期事业,诺贝尔基金会的官方出版物和《大英百科全书》等标准参考书在细节上有一些分歧,但有一点共识,就是他成了一名机械和化学工程师,为父亲处理爆炸物方面的工作。到了1867年,他已经在炸药方面获得了一项专利,这也为他带来了巨额财富。
据统计,诺贝尔一生中获得了355项专利,显然他对这些专利进行了大力开发。据说他兴建了90家工厂和企业,覆盖了五大洲的20个国家,是创立跨国公司的先驱者。尽管这些活动影响了诺贝尔从事科学研究、取得新发明的时间,但是要获得相匹配的经济回报,这些牺牲却是必需的。因此,对诺贝尔来说,科研本身似乎已经不再是一项可以全情投入的爱好了。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他去世前一年的1895年11月27日立下遗嘱,遗嘱公布后,亲属们都吓了一跳,他们只分到了价值3100万瑞典克朗的总资产中的100万克朗。除了家属有可能质疑这份遗嘱,对于执行人来说,他们至少还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第一,遗嘱的司法管辖权;诺贝尔幼年离开瑞典,此后也从未成为任何国家的合法居民。第二,资产的清算问题以及遗嘱中所谓的“安全证券”并未给出定义。第三,基金的管理以及奖金分配规则的建立。令财产执行人惊讶的还有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要担当的角色。很明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化学工程师拉格纳·索尔曼、机械工程师鲁道夫·利耶奎斯特以及诺贝尔的助手被诺贝尔指名担任执行人。鲁道夫·利耶奎斯特在1895年创立了电化学公司,诺贝尔曾为其公司投入了相当数量的资金。然而,这两位工程师并没有在诺贝尔奖的建立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执行人聘请了卡尔·林德哈根担任遗产律师,他领头协商并起草了实际的颁奖程序。当时林德哈根的政治生涯刚刚起步,他似乎秉持着最公正的立场来履行诺贝尔的遗嘱,他的家庭和朋友圈使他可以方便地联系瑞典科学界。他的叔叔是一个天文学家,在皇家科学院担任秘书。他的父亲是斯德哥尔摩大学一个科学研究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林德哈根自己也在这所学校担任了十年的秘书。在这里,他和S.A.阿雷纽斯教授以及O.彼得松教授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两位教授后来都成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委员会里很有影响力的元老成员。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硬科学而非工程学的代表们就已经获得了这位拥有特殊的权力来成立诺贝尔奖颁奖机构的人的青睐。

《诺贝尔的遗嘱》(2012)剧照。
林德哈根继续起草章程,为执行者和颁奖机构之间的协商提供基础。对于这两者的合作,诺贝尔或多或少预料到了一些。林德哈根和索尔曼努力划分了预料中会引起争议的不同领域的奖项,尤其是,他们尝试定义“物理学”“化学”等内容,但在最终和授奖机构的协商中,这些内容大部分都被删去了。对于授奖机构的科学家协商者而言,要更清晰地阐述获奖者的发现、发明和进步具有何种重要性,是一件难以确定的事。他们习惯了科学协会主要依据过去—有时是很长时间以来—的表现授予荣誉,而且尤其注重那些记录在已发表著作中的成绩。在最终的章程中,只有已经发表的作品才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条款对于工程师来说当然不是最有利的,因为比起发表论文,他们更倾向于在机器和建筑中实现自己的想法。
最后,基于各方一致同意的章程建立了一个组织架构,而并未设定对最终颁奖领域和成果的选择规则。1900年6月29日由瑞典及挪威国王奥斯卡二世颁布的《诺贝尔基金会章程守则》开头这样写道:“诺贝尔基金会,基于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博士和工程师最后的志愿和遗嘱所成立。”
尽管这份章程引用了遗嘱的相关段落,并且不断提到遗嘱的内容,但是,与对遗嘱本身的恰当解读相比,人们还是更加关注管理奖项的机制,以及诺贝尔基金会成员的人员组成和其享有的权利等内容。诺贝尔基金会一旦建立,它就将实现而且也确实基本上实现了自我管理,这也导致基金会此后难以从构成上或思维上发生改变。不仅如此,章程的第十部分还指出:“对评审员的颁奖决定不得提出抗议。如有不同意见,不应出现在议程记录中,也不应以任何方式让公众知晓。”
于是,由民众授权组建起来的诺贝尔奖机构,却不鼓励任何的民众监督机制。只要机构在他们狭窄的、自我定义的同侪范围内保持着秩序和理性的表象,尤其是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领域,那么这些领域以外的人想要加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就是天方夜谭。在这个奖项颁发的前15年,物理学和化学委员会的成员当中只有一位被看作“工程师”,即在1913—1924年服务于此的A.G.埃克斯特兰德,并且他也确实没有在决定性的政策制定中起到什么重要作用。直到今天,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章程守则》,科学类奖项的获奖提案,也就是提名方案的提交权只有经过选拔的小组成员才享有,而组内包含工程师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显然,诺贝尔奖的政治生态以及它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简略的遗嘱中变为现实这件事与工程学的利益是相违背的。如果诺贝尔的遗嘱表述更清晰、更严明,或许他就能更明白具体地表述“发明”“发现”和遗嘱中的其他词语所要表达的意思,或许他就能够阐明工程师是否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加入遴选委员会。事实证明,这份遗嘱不准确的措辞使得那些打算掌控提名过程的人依循自己的利益改变了它。诺贝尔基金会的一份出版物甚至承认“如果这份遗嘱是用严格的法律形式书写的,那么它可能就无法适应当今这个时代了”。而它是如何适应的当然就取决于谁掌控了适应的过程。
为什么工程师团体要求设立单独的诺贝尔奖项?
科技这一研究领域包含了有获得诺贝尔奖潜力的方向,但是产生的诺贝尔奖却少之又少。为工程师颁发诺贝尔奖以奖励他们对工程学(科学)做出的贡献,在诺贝尔奖颁发早期是一个公开讨论的问题。1908年一篇题为《诺贝尔奖的目的》的社论出现在《纽约论坛报》上。其中一部分写道:
诺贝尔基金会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忽视了诺贝尔本人的专业出身……诺贝尔至少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人们可能认为,他会因自己对人类做出的贡献而受到那一科学分支的信徒的欣赏,比如在发展先进的交通工具以及制造设备方面做出的贡献。他或许没有想到那一段历史已经过去。因为作为一个有像他那样的经历的人,对其他学科展示出偏好多少显得有一点奇怪。
很明显,早年间基金会也感受到了来自工程师的压力,19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的提名遭到否决,大家支持的是瑞典发明家尼尔斯·古斯塔夫·达伦,因为“他发明的自动控制器和储气罐为灯塔和航标提供了照明”。但无论是这一次,还是1909年古列尔莫·马尔科尼和费迪南德·布劳恩因“他们对于无线电报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获奖,在诺贝尔奖的获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举例来说,飞机的发明就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可,这明显是因为(委员会认为)它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超过了它可能为人类带来的益处。这样的想法十分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正是炸药的破坏性力量造就了诺贝尔奖。而粒子物理学和原子物理学的发现即使产生了那样的后果(原子弹),却也获得了如此多的诺贝尔奖。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工程师团体强烈要求设立一个单独的诺贝尔奖项。但是对于新奖项的诉求几乎可以说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每一个领域的群体都希望能设立本专业独立的奖项,而诺贝尔基金会并不乐意(增设奖项来)降低奖项的含金量。1969年,人们在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奖项之外添加了一个单独的奖项,但从技术上来讲,这并不是诺贝尔奖,而是“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的瑞士银行经济学奖”。不过,似乎只要是与诺贝尔的名字相关的奖项都会引起争议,一些经济学家竟然呼吁废除经济学奖,因为他们认为缺乏杰出的候选人。而且这一领域对于优秀与否的评价标准充斥着政治和社会的价值判断,因此难以做出客观的评判。
增设经济学奖属于特例。在1983年,时任诺贝尔基金会执行主任的斯蒂格·拉梅尔在一次发言中说,基金会在若干年前已经决定不再设立更多的奖项。因此,工程师的诉求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实现,1986年,他们要求设立单独的工程学奖的申请被正式拒绝了。
两年后,美国国家工程院设立了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奖,后来被称为“工程学的诺贝尔奖”。这个奖项是为了纪念来自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的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的捐赠而设立的。德雷珀奖每两年授奖一次,“用于奖励为人类福祉做出杰出工程学贡献的个人”。第一届德雷珀奖在1989年被授予了两位工程师,杰克·基尔比和罗伯特·诺伊斯,他们独立发明并改进了集成电路。后来的奖项分别颁发给了喷气发动机、计算机语言Fortran以及通信卫星技术的相关工程师。但是比起每年诺贝尔奖公布时狂热的媒体报道,这些奖项的公众认知度还很小。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如此渴望人们认可工程师的成就,却事与愿违,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本文选自《再造世界:工程师的冒险》,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美]亨利·波卓斯基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