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以恢弘的历史写作著称。他的新作《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下文简称《大分离》)探究了从公元前15000年前古代先民进入美洲大陆到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场不为人知的影响巨大的实验。在此期间,新旧大陆的人类先祖生活在彼此隔绝的时空里,面对着各异的地理、气候、动植物群落,各自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人性、思想和社会。
11月23日(周四)19:30,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第170场活动,我们联合译林出版社、微信读书,邀请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历史作家张明扬,与主持人、“彼得·沃森思想史”系列责编陶泽慧进行了一场线上对话。

对谈以《大分离》这本书为原点,谈及了不同大陆的文明缘何有巨大的差异,谈及了文明发展史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何启迪。对谈中嘉宾们提到,所谓“文明的冲突”也许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人类有极强的可塑性和适应性,“冲突”也许并非必然的结局。下文为活动回顾,内容有删改。
亚欧大陆文明与美洲大陆文明,缘何有巨大差异?
陶泽慧:您在《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中提出了大分离的观点,请问“大分离”的内涵是什么?
彼得·沃森:我确实同意从广义上来说,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样的,无论我们在肤色或者身材方面具有怎样不同的特征,人类在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从这一基础出发,我们可以探讨其中的一些差异。
第一个差异源自这个世界在地理方面的一个基本设定。美洲新大陆是一片从南向北延伸的狭长大陆,而我们的亚欧旧大陆基本上是东西走向的,而且它地处温带地区,不是热带地区。这片地区的气候基本上由季风雨季所主导,受温带气候的影响,四季非常鲜明。
由于气候循环,我们亚欧大陆拥有春夏秋冬,万物会在秋天走向凋敝,动物在冬天会开始冬眠。所以亚欧大陆在思想方面就非常关注丰产的问题,关注世间的万物是否还会生长。所以大多数的旧大陆宗教都是一类关于丰产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犹太教会有割礼仪式,因为它是一种丰产仪式。
相反的是,在美洲新大陆,万物生长的区域同时也是危险气候肆虐的区域。那里有风暴,有飓风,还有地震和火山。所以,当亚欧大陆的宗教主要崇拜丰产或关注丰产时,新大陆的宗教则主要关心如何让这些危险的气候平息下来,这是一个重大且根本的区别,这其中牵涉的一个重要差异关乎情感。总的来讲在亚欧大陆,人们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大体上是感到满意的。因为只要春天来到,万物确实会复苏并生长。虽然他们不了解背后的科学原理,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崇拜是起作用的。但是在美洲,人们显然对于天气知之甚少,并认为它们可能是诸神的愤怒,所以他们会为了阻止恶劣的气候再次发生而进行崇拜或祭祀。但是恶劣的气候总是会再次发生,所以他们的宗教屡次失败,他们的信仰体系也屡次失败,因此不断地走向极端。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祭祀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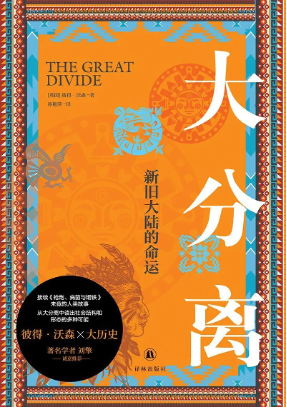
《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
作者:(英)彼得·沃森
译者:孙艳萍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3年5月
两块大陆之间的第二个重大的区别是生活在亚欧大陆的人非常幸运,这片土地上拥有五六十种可供驯化的动物,比如说马、绵羊、牛、山羊诸如此类。然而在新大陆,人们没有上述那些可供驯化的动物,他们面对的更多是野生动物,比如说美洲虎、野牛,还有鲑鱼等。它们都不像旧大陆的动物那样得到驯养,而那些被驯养的动物构成了旧大陆文明的基础。
这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来举一个小例子,也许它不算小,不过是一个单独的例子。因为美洲人没有大型哺乳动物来帮他们拉车,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发明过轮子,他们缺少可以拉车的动物,轮子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地理和动物群落如何决定了人们的思想生活。我是说,美洲人并不是因为愚蠢才没有发明轮子,而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轮子。
在谈论下一个话题之前,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在冰河时代结束的时候,海平面大幅上升,这就在世界各地——不管是旧大陆还是新大陆——都创造了很多三角洲和河流,不过旧大陆的河流数量比新大陆更多,这些三角洲就成了旧大陆驯化禾本植物生长的理想土壤,比如牧草、小麦等。因此,这些三角洲的区域就变得非常肥沃,同时它们还毗邻海洋,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些三角洲也促进了不同海口之间的贸易。然而在新大陆,人们倾向于种植块茎植物,而这类植物更喜欢生长在内陆湿润的土壤里,因此他们的文明没有在海口附近发展,贸易发生的概率也要低很多,因为他们只能沿着河流上下移动,而不会横跨海洋。通过这点大家可以看到文明间的巨大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大分流”与“大分离”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陶泽慧:其实越是宏大的历史潮流,越不容易被我们普通人所察觉,而识别和阐释这样宏大潮流的能力,就成了出色的历史学家必不可少的禀赋。我想问一问张明扬先生,在您的历史阅读当中,除了您最近读过的这本《大分离》以外,还有哪些历史作品提出了堪称宏大的观念?
张明扬:我想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的阅读来说,有一个和本书的名字很接近的名词——“大分流”,自引进以来一直有巨大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在刚刚接受历史教育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就是中国为什么在近代工业革命中落后了,也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大分流”理论走出了所谓的西方中心论,站在中国中心论来讨论这个问题,它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原本没有那么落后,本来是有机会的。这个理论刚引进的时候很多人非常吹捧这个理论,但是也有中国学者理智地分析这个理论的不足之处。在吹捧之中,依然有冷静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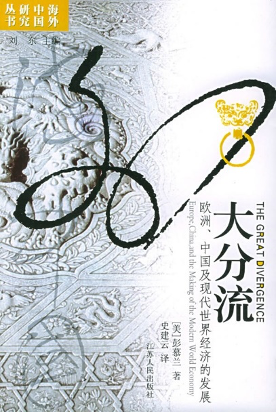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作者:(美)彭慕兰
译者:史建云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年3月
陶泽慧:彭慕兰先生提出的“大分流”概念在中国确实很受欢迎。我记得当时引进的时候,在中国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我觉得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在于,他认为西方在近现代所取得的事实上的领先,并不是源自于某种固定的种族或制度上的优势,而是因为一些历史偶然。所以说他的理论有一种打破历史宿命论的感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一种偶然性在里面。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人反思说,这种解释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向彼得·沃森提几个问题,一个是您怎么看待彭慕兰的“大分流”观念?您在书中提出的“大分离”观念,不知道有没有受过它的影响?而且无论是“大分流”也好,“大分离”也好,都分析了不同的地区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您觉得这两种分离的成因上有什么差异或者相似之处?您的“大分离”是不是对旧大陆的中心主义提出的反思?
彼得·沃森:我认为“大分离”和“大分流”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因为大分离指的是发生在数千年前的事件,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了当时的基础性宗教和经济,最终结出的果实是旧大陆的农业发展远远比新大陆更先进。
当然我们作为西方人,实际上对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中国社会直到公元1000年前都在以比西方更快、更复杂的方式发展着。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火药和纸张,以及各种由聪明的中国人发明的东西。
西方学术界其实提到了两种与“大分离”无关的分流理论,一种理论发生在12至14世纪期间,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这种分流是由瘟疫造成的。瘟疫对亚洲的影响远远大于它对西欧的影响,因此滞缓了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另一种理论认为,许多学术知识从中国传播到印度,到波斯,到埃及,再到希腊和罗马,换言之,学术中心沿着伟大的贸易路线向西转移。因为旧大陆有一条伟大的贸易路线,基本上东西走向,沿着地中海,经过红海,顺着阿拉伯海沿海,绕过印度,走向中国。这是古代世界的伟大的贸易路线,中国是这条路线的起点。然而彭慕兰的观点讲的其实是比这些都更晚近的事情,他所说的“大分流”发生在18、19世纪,而它的源头主要来自工业革命的兴起。众所周知,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为何由英国而起有多个原因,其中一种解释认为,科技革命主要诞生于17世纪的英法两国。所以历史确实有着很多种走向。
我认为“大分流”之所以同“大分离”截然不同,是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美洲从族裔的角度来说,已然是欧洲的一个部分。因此它也对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做出了贡献,然而我们所说的大分离恰恰发生在新旧大陆之间。而大分流发生在东西方之间,两者所讨论的实体不可同日而语。
陶泽慧:从“大分离”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新大陆的文明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也一直吸引着我的目光。人类并不是一块铁板,新旧大陆之间人性的差异,其实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也是相关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所以我想问问张明扬先生,在阅读《大分离》之前,您还觉得哪些关于新旧大陆文明差异的作品对中国人有比较大的影响?
张明扬:我在看这本《大分离》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书的全名为《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下文不再说明),然后我就把这本书也拿了出来一起读。刚才沃森先生说的很对,“大分离”和“大分流”之间的区别是很大,但我觉得这个《枪炮、病菌与钢铁》关注的话题跟《大分离》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地域来说都很接近,所以我觉得这两本书是可以一起读的。
这两本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过去我们的研究受限于学科设置原因,很少有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所以这种跨学科的分析框架对我们的冲击很大。《枪炮、病菌与钢铁》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征服了美洲,而不是反过来美洲征服了欧洲。对中国人来说,这既是一个显学也是个很陌生的话题。这本书运用了多角度的分析框架(比如气候环境),并不仅从我们关心的文明说起,这样的分析框架在《大分离》中也有所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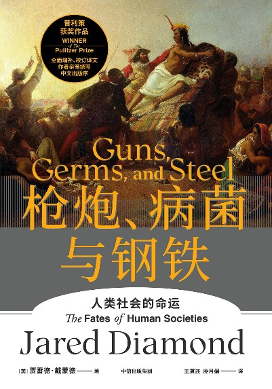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作者:(美)贾雷德·戴蒙德
译者:王道还/廖月娟
版本:中信出版社·阅微 2022年1月
陶泽慧:《枪炮、病菌与钢铁》确实是一本中国读者非常耳熟能详的作品,我记得关于大陆走向的问题,无论是在那本书还是沃森这本书中都有所探讨。我想问一问沃森先生,您觉得《大分离》在哪些方面与《枪炮、病菌与钢铁》产生了观点上的碰撞?
彼得·沃森:首先我要说,《大分离》和《枪炮、病菌与钢铁》在观点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分歧。《枪炮、病菌与钢铁》确实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我觉得我把他的论证推得更远且更为完善了一些。
我正在写一部《英国思想史》,我需要首先在书中向大家表明英国到底是在多晚才变成思想的主流阵地的。我们知道,在此以前的很多年间世界上的思想领袖都是中国人,发明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数字的是印度人、波斯人,发明我们的律法和哲学的是希腊人和罗马人。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发生在亚欧大陆相对东部的地区,而不是西部地区。而粗略来说,差不多在过去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才开始步入主流。现在,西方已经闪耀了1000年左右,但是现在的世界正在发生改变,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崛起,看到了非洲的崛起,还有伊斯兰教无处不在的痕迹。
我觉得造成了当初新旧大陆的大分离的种种因素,部分仍然存在,部分已经被取代了。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开始美洲是没有马的,是欧洲人把马引进到了美洲,然后美洲原住民欣然接受并驯养起了马。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北美大草原上看到大批的野马群,这些年来我们目睹了诸多的变化,有些源自大分离,还有些则源自大分流。这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当前的世界。
对于游牧民族的认知,我们有所遗漏
陶泽慧:我想请张明扬先生谈一谈,您在阅读《大分离》的时候,这本书的哪个部分对您来说最有趣?
张明扬:这本书的结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说旧大陆的历史是由“牧羊人”这个角色规定的,而新大陆扮演同样角色的是“萨满”。这些年很多中外学者在讨论亚欧大陆历史的时候,喜欢提到这样一个点:旧大陆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游牧民(也就是牧羊人)和定居人口(也就是农民)之间的冲突引发的。我觉得这和沃森先生的观点形成了有意思的呼应。
陶泽慧:沃森把游牧民族提到了中心,而且提出新大陆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定居文明。所以我想问沃森先生,您将游牧民视作亚欧文明前进的一股主要动力,并认为新大陆与此相异的文明模式对两片大陆的差异化发展带来了很重要的影响,那么,能否请您为我们详细讲一讲旧大陆与新大陆这种关键模式的差异?
彼得·沃森:如果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无误的话,刚才张老师提到了“大分流”是世界运行的一种方式,这点很对,但是当我们谈到游牧民族时我们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根据定义,游牧民族是跟土地相连的,他们的存在跟他们生存的地方是相连的,中华帝国是这样,奥斯曼帝国是如此,还有俄罗斯帝国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以陆地为基础的帝国。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分流”和“大分离”模式以外,在过去500年中,我们的世界还有一场非常巨大的运动,那就是帝国的运动。比如说像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帝国,它们不同于其他帝国,它们都是海洋帝国,它们以更为分散的形式遍布全球不同的地方。
它们会把先进的文明与没那么先进的文明整合在一起,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历史性相遇。比如说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还有西班牙,都会将自己更为先进的文明强加于更为原始的文明之上。因此就产生了目前我们所知的各种各样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确实会压迫原住民,定居下来,因此一种更为先进、庞大的文明就被引入一种更为原始、渺小的文明之中。所以我们当前看到的世界,其实是大分离、大分流和海上帝国的一个结合体,我们才有了如今这样一种诡异的全球化形式。不知道这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不过这就是我想给出的回答。
我认为,曾经有一度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的舞台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认为在近代他们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据我所知,游牧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生活方式,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南北迁移,由于游牧生活的定义,你不会拥有太多财产,而且游牧民族也很难生产任何可以长期留存的艺术,因为他们总是在移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他们自己最大的敌人。我不认为游牧群体可以仅凭自身的生存方式,而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面对冲突的困境,人类有更强的可塑性和适应性
陶泽慧:沃森先生除了《大分离》以外还写了很多其他鸿篇巨制,其中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可能就是他两部非常宏大的思想史作品——《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以及《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前者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开始一直讲到19世纪末,而后者重点关照了离我们最为切近且风云变幻的20世纪。《大分离》是一种文明史写作,而《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和《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属于思想史写作,沃森先生觉得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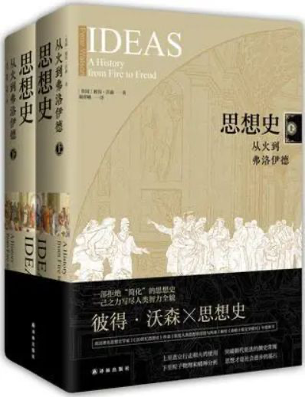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作者:(英)彼得·沃森
译者:胡翠娥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彼得·沃森:我不太确定,但我觉得主要的区别在于,如果你在写作思想史的话,你写的是人,是人脑子里的思想。而《大分离》则主要写的是自然,以及自然与人性的关系。文明史写作不仅仅书写自然与思想的关系,它还关注生活的方式,人们如何一起生活,如何适应环境。《大分离》讨论的是那些导向文明的情景,而根据定义,文明指的正是人们如何借助一系列思想而生存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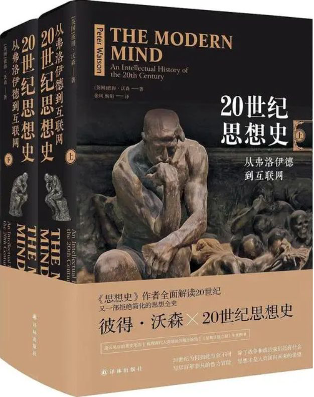
《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作者:(英)彼得·沃森
译者:张凤/杨阳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
陶泽慧: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学者把我们的目光从相对遥远的过去拉回到现在,聊一聊历史对于我们当下所处的生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想先问一问张明扬老师,您看从2022年到2023年,世界经历了俄乌战争,又爆发了巴以冲突,战争始终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野。它就好像人类族群之中始终存在的一种互动模式,不会离我们远去。您写过中国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冲突和动乱,您觉得我们在这些冲突和动乱当中,应该关注哪些文化要素?
张明扬:第一点我想说,长久以来我们很喜欢讨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我们越来越感觉文明的冲突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会不会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倾向?我们越认为文明是不可兼容的、会有冲突,最后反而会导致不好的事情发生。
第二点我想说,我希望看到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自我反思精神。我觉得我们讨论了几本书,无论是《大分离》还是《大分流》,还是刚才说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我觉得它们都有文明的自我反思,《大分流》刚引进的时候,中国学者也对大分流产生了一些反思,对中国文明也产生了一些自我反思。所以我觉得文明的一个自我质疑与自我反思是当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要总认为我们的文明最好,别人文明不行。
第三点我想说,对外来文化和文明我们应该有一种宽容的态度,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想我们对外来文明的融合是否是一件好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陶泽慧:我觉得张明扬老师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观念的力量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相信冲突不可避免,那冲突确实是有可能不能避免的。但是如果你擅长反思的话,你就始终能够从冲突中退一步,来想想自己也许并不永远都是对的,我们也有可能会犯错。以及最后讲到的宽容,与这两种心态都非常相关,宽容就是我们既不希望被别人伤害,但我们同时也不希望去伤害别人。
最后我想把发言的机会留给彼得沃森先生,沃森先生,您在《大分离》中提到学界有一种倾向,就是希望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共性,而不是差异,但您觉得差异反而更具有启发性。当前国际社会确实冲突不断,包括民粹主义也不断地在各个国家蔓延。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尊重不同国家的文明,并且求同存异显得尤其重要。您觉得在这方面,您的著作能够为读者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彼得·沃森:我觉得我的书体现出我们人类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我们能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应对各种不同的环境。我们人类不仅具有可塑性,而且还有很强的适应力。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利用好我们的可塑性,更好地适应彼此,适应共存。
最近我一直在写大英帝国。当英国人前往海外探索未知的土地时,他们本性中有着善良的部分,他们会对其他人感兴趣。但是在一切相遇的背后,根源还是有关土地和贸易,这也就为冲突的发生提供了舞台。所以,我们要运用好我们的适应力。我记得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只是我不记得书名了,它写的是帝国子民在海外发现的各种技术,比如说葡萄牙人对某类东西感兴趣,西班牙人对另外一类东西感兴趣,英国人有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而他们感兴趣的都是他们本土所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人类是一个奇异的组合,我们既有相似之处,彼此也有差异性。这本书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要区分清楚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
种族中心主义其实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种族主义是一种包含敌意的版本。所以我想传达的主要观点是,我们作为人类已经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如今我们面对着一种新的环境,当下全球人口已经达到历史新高,这就导致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会在彼此间产生冲突,我们必须要适应这些新的现实。而我的书展示的是,我们拥有这样的适应力,我们不应该认输并停止抗争,我们应该努力地彼此适应,努力共存。
扫描下方二维码,收看回放

作者/彼得·沃森、张明扬
编辑/张进
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