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被误读是知识人不可完全避免的命运,那么这命运的痕迹在施特劳斯身上可能尤其明显。很少有一位哲学家像他那样,作为上世纪“神学复兴”产物的他,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还有一层模糊不清的神秘感,在被议论的同时,也被往各个方向曲解。
人们围绕施特劳斯发起过哲学抗议,认为他以一种自然法的传统教诲为伪装,隐秘地引入来自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国家主义。更常见的哲学指控是,施特劳斯试图“传授某种包含危险的反民主情绪的隐秘教诲,以及他认为应该明智地使用宗教和其他‘高贵谎言’以控制民众”。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施特劳斯被翻译引进到汉语学术界,也曾遭遇误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被认为是一个彻底批判、否定现代文明及其知识体系的人物。
施特劳斯见证并预见了现代文明存在的问题,认为其若要继续保持活力,免于毁灭,必须需要某些前现代的传统权威。对他的批评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此。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年9月20日—1973年10月18日),20世纪犹太裔德国哲学家。
施特劳斯于1899年9月20日出生在德国黑森州的基希海恩镇,在犹太家庭长大,接受了“一战”前的文理教育。他在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待过,年近四十,才得到第一份教职。
如今谈起施特劳斯,他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可能一样多,对其看法也一样激烈。
当今的哲学研究者史蒂文·史密斯,一直在为施特劳斯辩护,认为施特劳斯理解的哲学并非一种建构性的或构造性的活动,而更多是一种怀疑性质的活动,也即哲学是“原初意义上的怀疑”,知道自己不知道,或知道知识的局限。他认为,“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他并不否定实证精神和历史意识)制造了一种人造的洞穴,是柏拉图自然洞穴之下的人造洞穴。在自然洞穴,人们看到的是投射到墙上的影子而非真实世界,而人造洞穴使人连自然洞穴也够不着。
他追求的是整体性知识,不是为了得到具体的答案,而是追寻这个过程。也因此,施特劳斯不停地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古早”的定义,在他的年代已经被丢进历史的“废物站”了。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新书《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相关章节。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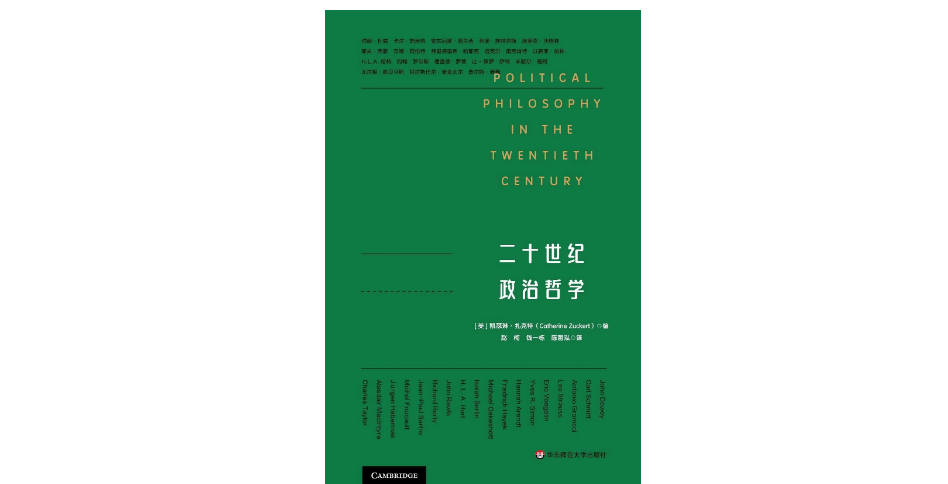
《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美]凯瑟琳·扎克特 编,赵柯、钱一栋、陈哲泓 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
哲学是最初意义上的怀疑
大约三十年前(指1985年——摘编者注),英国批评家伯恩尼特(Myles Burnyeat)在《纽约书评》上发文怒斥施特劳斯。伯恩尼特说,别的不说,施特劳斯连哲学涉及什么都不懂,尽管施特劳斯的作品拥有很多关于“哲人”的讨论,但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知道哲学的涵义”。如果伯恩尼特所言不虚,那这将是一项致命的指控。但问题在于是否真的如此,以及伯恩尼特在“哲学的涵义”这个问题上的自信是否站得住脚。
伯恩尼特并没有费心定义他所理解的“哲学的涵义”,但他想的无外乎是下面两种可能中的一种。首先,二战以后,哲学这个词,至少在英美世界,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奥斯汀(J. L. Austin)和后期维特斯根坦的日常语言进路的决定性影响。哲学意味着对日常语言中的概念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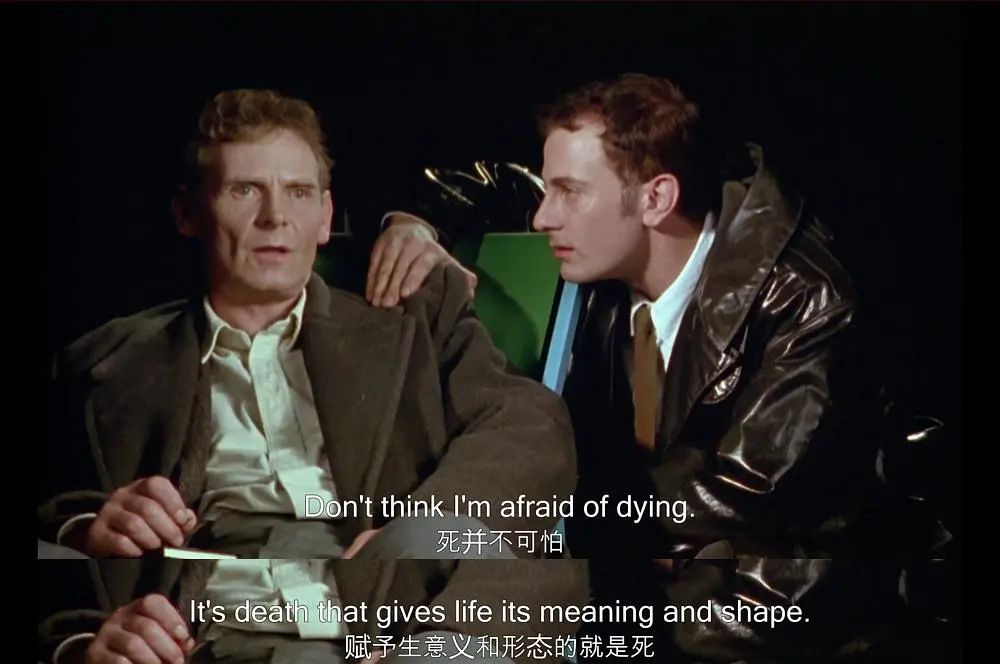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剧照。
这场分析运动假定,所有的哲学问题本质上都是语言问题,都可以通过对日常用法进行更仔细的检查而得以解决。最近,一些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违背日常语言进路——选择进行更雄心勃勃的重建尝试,以解决实质性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已经尝试参与这种公共讨论。
施特劳斯显然不是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哲学家。施特劳斯对哲学的理解,回到了哲学较为古老——很古老——的含义。在最古老的意义上,哲学是philo-sophia,字面意思就是爱智慧。但是,爱智慧意味着什么?在远未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一门学科之前,哲学与一种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实践哲学并不一定意味着坚持某套特定的学说或方法,更不意味着坚持某个思想体系,而是实践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哲学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练习,还是一种实践性的练习,旨在回答这些问题:“我应该如何生活”,或者“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或者仅仅只是“为什么是哲学”。
最近,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老观念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法国古典学家阿多(Pierre Hadot)在《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中提出,古代的哲学流派——柏拉图主义者、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都首先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精神练习”。这种精神练习的目的是让灵魂得到解放,让门徒摆脱激情的桎梏。他们的目的是建立精神团体,大家聚在一起可以寻求过一种逍遥的生活,并与其他选择了相同生活方式的人建立友谊。与此类似,内哈玛斯(Alexander Nehamas)也试图恢复哲学作为“生活艺术”的理念。他虽然否认自己是在敦促读者返回哲学的生活方式,但他想要特别提醒那些分析哲学家,一个人所拥护的哲学类型最终会影响到这个人的类型:哲学话语和文学巨著一样,塑造着人的性格。根据内哈玛斯,哲学作为生活艺术最伟大的倡导者是苏格拉底、蒙田、尼采和福柯。

《苏格拉底》(Socrate,1971)剧照。
只有当我们从这种较为古老的意义上理解哲学,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开始欣赏施特劳斯在最近的哲学辩论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过,对于施特劳斯而言,哲学不是阿多意义上与古代某些禁欲主义邪教相关联的“精神练习”,也不是内哈玛斯所坚持的作为个体自我建构形式的“哲学的生活方式”。根据施特劳斯的理解,哲学与其说是一种建设活动,不如说是一种怀疑活动。对于施特劳斯而言,哲学是探究性的;用他的话说,“是原初意义上的怀疑”,也就是,知道自己无知,或知道知识的限度。哲人的任务与其说是提供答案,不如说是预测问题。一旦对解决方案的确信胜过对其中问题的认识,哲人就不再是哲人。从许多方面而言,这都是一个严谨、苛刻的哲学概念。用现代范畴表达苏格拉底式洞见,那就是哲人必须是“否定辩证法”的实践者。
施特劳斯曾在一段话中将哲学定义为“原初意义上的怀疑”。这段话提供了理解他如何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关键。他回答了下面这些问题: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它对追随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有什么样的承诺和责任?最为根本的是,什么能够证明选择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
一种关于“整全”知识的
爱欲活动
施特劳斯当然是作为一名政治哲学的学徒而出名,但他对政治哲学的理解离不开对哲学的总体理解。施特劳斯解释道,哲学是对“普遍知识”或关于“整全”的知识的追问。所谓“整全”,不是指关于每种存在物的百科全书式目录(附带解释的分类目录),而是指关于“事物本质”,即存在(being)之基本范畴的知识;正是存在的基本范畴这个问题,让我们提出“……是什么”这种形式的问题。我们通过知晓事物的本质或其所属的范畴来知晓该种事物。哲学追求的是范畴性知识,而不是关于事物特殊性的知识。

《会饮》(Le Banquet,1989)剧照。
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事业出现,是因为关于这些本质的知识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拥有关于万事万物的众多意见,它们或多或少是可靠的,但这些意见往往表现出内在的矛盾,甚至相互矛盾。在施特劳斯著名的表述中,哲学是“试图用关于整全的知识取代关于整全的意见”。但是,从根本上而言,整全是难以捉摸的,虽然哲学追求关于整全的知识。我们可能拥有关于部分的知识,但整全依然是神秘的;我们虽然拥有关于部分的知识,但如果没有关于整全的知识,那关于部分的知识就是不完整的知识。
施特劳斯承认,志向是崇高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两者落差之大,“可以犹如西西弗斯式的或丑陋不堪的”,但他接下来断言,哲学“必然有爱欲相伴左右,通过爱欲得以维持,并因爱欲而上升前进”。换句话说,哲学首先是一种爱欲活动,它更多地是对知识的追问和渴望,而不是智慧的达成或获得。
施特劳斯有时把哲学和某种因果知识联系起来。“哲学家最主要的激情是对真理的渴望,渴望认识永恒秩序,渴望认识整全永恒的原因。”施特劳斯再次强调了作为哲学特征的那种特殊欲望或激情——爱欲。这种激情渴望认识整全的原因,而非任何特殊的事物。实际上,这种激情导致哲人睥睨与永恒秩序相比“渺小、短暂”的人类事物。由于主要关注原因——关注事物的形式(form)或艾多斯(eidos),哲学似乎很少关心万事万物,包括人类事物的个性。
施特劳斯意识到了——深深地意识到了——对这种哲学概念的明显反对。哲学是“关于整全的知识”或“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这种古老或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概念似乎预设了一种“过时的宇宙论”,即宇宙是一个有序的宇宙,人类和其他物种扮演各自的角色。现代的宇宙论与此截然相反。现代的宇宙论认为宇宙是无限膨胀的。如今,目的论的自然观就如神创论及其他伪科学的主张一样过时。那么,施特劳斯是否对这种非常尖锐的反对意见进行了回应?
向“自然洞穴”爬升

《苏格拉底》(Socrate,1971)剧照。
他的确有所回应。施特劳斯否认古典人性论预设了任何特殊的宇宙论或潜在的形而上学。对整全知识的欲望仍然只是一种欲望;它不是武断地预设,更不是宣称要证明一种或另一种特殊的宇宙论。毫无疑问,现代自然科学以培根和笛卡尔所设想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相对于自然的力量,但这并不能保证科学提供了对自然、包括对人性的全面理解,除非把力量等同于理解。施特劳斯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古人也考虑了这样的科学观,但因它乃是“对人性的破坏”而拒绝了它。
施特劳斯提出,古代哲学与现代科学不同。古代哲学从“追问宇宙论”的角度,而不是以通过回答宇宙论问题的方式来理解人类处境。正是这种对整全知识的开放或怀疑态度,将古人与现代自然科学区别了开来:
无论现代自然科学有多重要,它都无法影响我们对人身上的人性的理解。对现代自然科学来说,以整全的眼光来理解人意味着以低于人(sub-human)的眼光来理解人。但以这种眼光来看人,人作为人完全不可理解。古典政治哲学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人。这肇始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远远没有致力于某种特定的宇宙论,以至于其知识是无知之知。无知之知不是无知,它是认识到真理和整全难以捉摸。
施特劳斯对哲学的理解开始于渴望获得关于整全的知识,结束于意识到“真理不可捉摸”。他如何得出这个结论?

《禁忌》(Tabu: A Story of the South Seas,1931)剧照。
关于部分的知识必定先于关于整全的知识。因为我们无法立刻获得关于整全的知识,就像“子弹从枪管子里射出来”(用黑格尔那个著名的比喻),我们必须采取“上升”的方式才能企及整全,也就是,从唾手可得的东西,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出发,朝晦涩不明、被神秘所包围的东西运动。哲学必须从已经得到普遍认同的前提出发,“辩证地”前进。这种上升运动的一开始,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些“第一位”的东西,比如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战争与和平的命令。“政治”的东西给我们提供了通向整全最清晰的切入点。为何如此?
政治哲学跟伦理学、逻辑学或美学不一样,它不单单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对于施特劳斯而言,政治哲学可以说是第一哲学。为了探究政治事务,首先必须探究关于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的意见看法,是这些意见看法塑造了政治生活,并给予政治生活以方向。一切政治都被意见所左右,政治哲学的起点就是探究统治共同体的各种意见——这往往是在法律、法规和其他官方文件中所传承下来的权威意见。这些意见虽然不是哲学本身,但却分享了哲学的一些东西,那就是,对政治善、共同体之善的关切。然而,把政治哲人和最好的公民(或政治家)区分开来的,不是知不知道如何让这个或那个政治共同体获得福祉,或关不关心这个或那个政治共同体的福祉,而是具不具备一定广度的视角:追寻实现“好的政治秩序”的“真正标准”。
政治共同体从一个角度看是存在的一种范畴,只是整体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整体的缩影。政治是自然秩序中最综合最齐全的人类组合。因此,政治秩序为其他所有秩序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或等级。在所有有朽事物中,政治秩序异质性是永恒秩序异质性的最相近表达。对整全的认识必须从政治哲学开始。不过,政治哲学是成为目的本身还是成为理解形而上学的手段,这个问题施特劳斯没有明确解决。
施特劳斯在很多作品中强调,他的哲学方法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著作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达。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在首位,而是因为他们站在特别好的位置上,可以直接触及那些塑造了他们所在共同体的政治意见。施特劳斯称,政治意见塑造了“自然意识”或“前哲学意识”。从政治意见中,出现了哲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政治意见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得以出现、得到对照的视界范围。古典政治哲学直接与政治生活相关,但之后的所有哲学都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改造,因而只能间接地体验他们的世界,可以说就像是通过一层玻璃乌漆墨黑地观察。自然经验又进一步被多次杂糅了神学、科学以及历史的哲学传统所扭曲。这样一来,我们如今通过概念棱镜来体验世界,概念棱镜阻止了我们进入与城邦面对面的哲学“原初状态”——对不住了,罗尔斯。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恢复这些意见,这种被层层理论抽象所封锁或包裹的“前哲学意识”?
施特劳斯的计划在于像剥洋葱一样,剥开被层层包围的传统(它成功地遮盖了它所预设的自然意识),某种程度上像卢梭的系谱学方法。总有一些天然的障碍阻碍哲学生活,未来也是:施特劳斯提到了自然而然的忽视,想象的力量,以及迷信。如今,阻碍我们进入哲学生活的是一系列完全人为的“伪哲学”——历史主义、科学实证主义、经济主义,它们扭曲了我们与经验的关系。施特劳斯自相矛盾地回答,只有通过历史研究——不是本着学术界所流行的历史主义精神所展开的历史研究,而是通过掌握仔细阅读的艺术所展开的历史研究,我们才能重新思考原初的哲学。只有通过阅读某些“古书”,我们才能开始缓慢而艰苦的上升,从我们现在居住的人为洞穴回到作为后来所有哲学之基础的“自然洞穴”。

短片《柏拉图的洞穴》(Plato's Cave,1990)剧照。
理性与启示的对峙
哲人或许相信——施特劳斯或许更相信,哲学生活乃是最好的生活。但问题在于,是什么使得哲学生活乃是最好的。施特劳斯提到了哲人的满足感,一种近乎“自我陶醉”的满足感。
但这与其说是一种证明,不如说是哲学生活的一种表达。知道自己无知如何有助于哲人获得满足感或幸福感,也不太清楚,但施特劳斯会说:“就算是那样吧。”哲学只是众多方案之一,除了哲学还有其他方案。哲学能够在其他方案面前,为自己及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吗?这也许是施特劳斯哲学著作的中心问题。
与哲学相对的另一种严肃方案,实际上也是唯一真正与哲学相对的方案,是神的启示所带来的挑战。与这个最严肃的方案相比,其他选择和其他生活方案,甚至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经典冲突,都变得微不足道。理性与启示,或者用施特劳斯惯用的说法,雅典与耶路撒冷,仍然是哲学在捍卫自身及自身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最尖锐、最复杂的对立。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区别,在于对道德在整个人类生活经济结构中起什么作用,持不同的看法。对耶路撒冷的信徒来说,热情地追求正义代表人性的顶点,但对于雅典的铁杆拥护者而言,道德最多只是有助于实现沉思性的自主。这个对立,这两者之争,而不是著名的“古今之争”,才是“哲学问题”,因为如果哲学不能在启示的信徒面前为自己辩护,那哲学就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基于武断决定或意志行为的信仰。

《自然权利与历史》,施特劳斯著,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7月。
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最直白地阐述了这种对立:
没有光明、指引和知识,人无法生活;只有借助于关于善的知识,人才能找寻他所需要的善。因此,根本问题就在于,人是否能够获得关于善的知识?没有这种知识,人仅凭自身的自然能力,不能指导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人类整体;或者说,人类是否依赖于关于天启的知识?最根本的是在人的指引与神的指引之间二选其一。
这样一来,哲学与启示之间似乎就有一种对峙。这两方都能驳倒对方吗?
像苏格拉底一样,施特劳斯考察了支持各方的观点。首先是从神学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在犹太传统中,所谓的“上帝的召唤”经常被认为是得到了一长串传统的证实。见科恩兄弟的电影作品《谋杀绿脚趾》(The Big Lebowski):“三千年的美丽传统,从摩西到山迪·柯法斯——你说的对,我活在过去。”时间顺序可能有点偏差,但这个意思很对。这一召唤是在西奈山上给摩西的,然后传给了约书亚,然后又传给了长老和先知,整个传统就是一条完整的链条,一直传递到拉比那里。这个传统可靠吗?

《谋杀绿脚趾》(The Big Lebowski,1998)剧照。
施特劳斯对这种历史证据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上帝的召唤与那些声称经历过召唤的人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只有有人声明受到召唤,召唤才是可靠的。但这就使得召唤取决于信徒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又不可避免地因人而异,因教派而异。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会解释得跟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大不一样。另外,那些声称自己见证过启示或继承了这种启示的人,已经是这种信仰的信徒了。除了信徒本身,不存在公正或中立的证人。
如果他是对的
施特劳斯考察并驳斥了为启示的优先性进行辩护的众多论点,但要是从哲学的角度看会如何?好不到哪儿去。哲学要求启示在理性、在我们人类理性的门槛面前捍卫自己。但启示坚决拒绝这样做。启示必须理性地证明自己,这是个循环论证。要证明的东西已经被用作前提,即启示是一种理性经验。哲学最多只能说驳倒了那些为启示进行辩护的神学观点,并没有证明启示本身是不可能的。
施特劳斯考察了几个更具体的反启示观点——出自对圣经的历史批评和考古批评,以及现代科学理论(达尔文主义),但他最为尊重哲学化的神学,或者说自然神学的主张。
施特劳斯不厌其烦地为启示做最有力的论证,这相当于为哲学创造一个尽可能高的障碍。他好像常常要求哲学背负更大的证明责任,而不是让神学背负更大的证明责任。神学只需要敞开启示的可能性,但哲学却要拒斥启示的前提。任何不足都必须被认为是失败。施特劳斯本人是20世纪早期“神学复兴”的产物。“神学复兴”与巴特(Karl Barth)和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eig)联系在一起,这两人“认为有必要考察,对正统神学——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批判,所谓的胜利在多大程度上实至名归”。施特劳斯显然理所当然地认为,神学批判方面的胜利还不实至名归。
虽然神学的复苏提醒施特劳斯启蒙在宗教批判方面的失败,但把他置于反启蒙政治神学的阵营中,说他是捍卫信仰者,那就错了,但有些人就是这么做的。出于对斯宾诺莎的不满,施特劳斯努力回到更古老的哲学概念,即探究性的哲学,而不是重申正统。我认为,这就是他所说的那个意思,即回归前现代哲学不是不可能,只是非常艰难。
施特劳斯向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他总是把这种回归描述为“试探性的或试验性的”,并不是对自然等级制度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古生物学或优生学的认可赞同。一般而言,他对古代哲学的理解与哲学的政治问题或“哲学生活”问题相关,而不是与关于政治的哲学相关。当然,这并没有阻止各路阐释者把各种立场强加到施特劳斯身上,从新保守主义到虚无主义的反现代主义。

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哲学就在街头巷尾》(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2008)画面。
施特劳斯明确指出,哲学生活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不断探究提问的形式。这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本义。这里,甚至探究主义(zeteticism)都不是向斯多葛派的那些问题的回归,而是向古人都不知道的一系列问题的回归,主要是雅典与耶路撒冷问题,或者他后来所谓的“神学—政治问题”(“我的研究唯一的主题”)。探究性或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并不声称找到了解决理性—启示问题的答案,更不声称找到了唯一的答案,而是让这个问题继续存在下去,以待未来不断考察。正是探究式的理解,使哲人免于信和不信这两种教条。这两者都不能经受理性辩护的考验。只有哲人,那生活在对雅耶之争的永恒意识、永恒互动中的人,才能证明哲学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施特劳斯是对的,即我们已经忽略了哲学生活这个问题,那今天很多人未能把他看作是一位哲人,经常误认为他是一个评论家、思想史家甚或某种政治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施特劳斯的兴趣不在于哲学技巧或方法,更不在于推进对概念和命题的认识,而在于这些东西的先决问题,“为什么是哲学”?对于军事战略或商业经营之类的活动,人们显然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目的(胜利、利润)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但是,哲学的目的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施特劳斯关心的是哲学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它赋予共同体生活以什么样的价值。他对这个问题专心致志的审视在最高程度上履行了哲学的职责。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二十世纪政治哲学》一书。
原文作者/[美]史蒂文·史密斯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