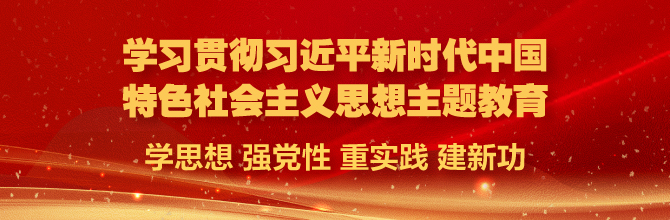“你觉得怎么样才算生态宜居?”“你觉得振兴的乡村是什么模样?”2021年5月,40多位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在北方的一个村庄里开启了一场特殊的调研,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尝试站在农民的视角,去了解风起云涌的乡村振兴中,农民心底真正的想法。
从带着书卷气的问题开始,他们在全国五省十个村庄中,和农民一起生活,学习农民的表达方式,一点点调整着问卷和访谈的方式,一步步走进乡村,去调研、分析、理解乡村,了解农民眼里的乡村振兴,如今,他们想要把农民的真实想法,讲述给所有人。
第一次遇到80岁的种田农民
午后的阳光照进宽敞的门洞中,一对八十岁的老人坐在阴凉里,他们刚刚从地里收工回家,吃完午饭,就迎来了入户调研的年轻学生。

中国农大的博士生董怡琳和一对80岁的老夫妻。受访者供图
这对八十岁的夫妻,是中国农大的博士生董怡琳在东部一个县调研的第二村遇到的,他们种着三四亩地,妻子还会接一些镇上小作坊计件加工的活儿。他们身体还不错,地里的粮食足够养活自己,还会打点儿零工,闲暇的时候,会把自家的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
这是董怡琳第一次遇到八十岁以上的农业生产者,尽管在大学本科、硕士期间,她也曾多次在乡村调研,但仍然为这对老夫妻的勤劳和乐观震撼。她告诉记者,她在北京看过很多文章,说在乡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正在不断弱化,但真正到了乡村才知道,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仍在依靠土地为生,土地的保障功能就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曾经和许多留守老人谈到过粮食的问题,有一位老人跟我们说,乡村还有这么多人,要是都能够种粮食养活自己,国家的粮食压力就会小很多。”
在农民眼里,乡村是什么样的?或许土地是了解他们最好的切入口,同样参加了调研的中国农大博士生陈诺,曾经访问过一位回乡的老人,这位六十岁的老人在北京打工三十年,到六十岁后,很难再找到活儿干,于是回乡务农,“这和我们理解的退休是完全不同的境遇,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在访谈中接了一个电话,对电话另外一头的人说,回家后工作不好找,活儿很少”。

中国农大博士生陈诺,正在为一位老人做调查问卷。受访者供图
六十岁意味着可以拿到每个月一百多块钱的农村养老金,但同时,他们更面临着就业机会的急剧减少,不论是外出务工,还是就近就业,都是如此,“在城市里的人也许很难想象,六十岁以后还要考虑就业的问题,但在乡村,大多数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只要体力跟得上,就必须继续干活挣钱,因为生计更重要。”
从一个最普通的村庄开始
这是一项名为“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的研究课题,从2021年3月开始准备,当年5月,40多位中国农大的师生就走进了乡村,他们住在村民家,和村民们一起生活,观察、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和想法。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刘娟,是带队调研的负责人之一。刘娟曾经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后在荷兰、美国、西班牙等做博士后、访问学者等,回国后又回到中国农业大学,从事农业与农村社会学研究。她参与了项目的全过程,从前期的准备,到选择调研对象,再到入村入户调研,最后整理资料、撰写文章等。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刘娟正在田间地头做调研。受访者供图
“尽管参与的师生,都有多年村庄调研工作的经历,但这一次仍然遇到了许多难题。选村就是其中一个。”刘娟说。
选择什么样的村庄调研,才能尽可能获得相对普遍性的结果?刘娟告诉记者,在最初试调研时,他们选择了一个熟悉的县,但县里的干部并没有理解他们的初衷,向他们推荐了全县做得最好的两个村庄。“这和我们的想象不太符合,发展较好的个案,确实有它的价值,但和我们这一次调研的目的有很大的区别。”最终,县里推荐的两个村庄,他们都没有去,而是另外找了两个较为普通的村子。
什么样的村庄是普通的村庄?一个正在探索振兴之路的村庄,没有政府重点打造的项目,没有无数的干部和年轻人进入村庄,没有大企业在这里兴办产业,大部分工作都要靠他们自己完成,这样的村庄,或许才是中国数十万乡村的普遍代表。董怡琳告诉记者,他们在河北试调研的第一个村庄,就无法找到调研人员可以留宿的地方,农民的房子都不是很大,大多刚够自家人住,因此,他们不得不到隔壁村寻找住处。
学会用农民的方式沟通
住进村里,并不意味着一切会按照设想的程序按部就班地完成。入村入户,仅仅是拉近了空间的距离,他们更要学习,怎样才能真正地像农民一样生活。
在参加团队调研时,张森刚刚拿到博士生录取通知书,很快就跟着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扎进了村里。张森没有在乡村生活的经历,尽管在本科和硕士期间,也曾做过许多乡村调研,但仍要学习怎么和农民打交道。

中国农大博士生张森在村民家中做调研。受访者供图
在一个曾经的贫困村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和张森聊了很久,张森一直尝试着按预先设计的问卷内容和老人交流,但老人大多数时候,都在自顾自地向他诉苦,老人的儿子早年赌博,欠了很多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村里给老人提供了很多帮助,老人自己也很感激,但依然很难彻底解决老人家里的问题。
和村民交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森告诉记者,“农民的生活世界很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宏大叙事当中捕捉他们的生活细节,所以在调研中,我们特别需要沉下心来,认真倾听并试着去理解、去感受他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
更多时候,他们需要配合农民的生活规律,跟着农民下地,在地头完成访谈。陈诺曾经在地头和一个农户聊了很久,那一次,她准备入户访谈的时候,发现家里没人,都下地了,她就找到地里,坐在地头和对方聊天,“那个访谈的农民,当时正在地里锄草,后来他在地里跟我聊了差不多一上午,他还拿了一个装化肥的编织袋给我坐,其实我并不介意坐在田埂上。”
董怡琳曾经访谈过一个忙碌的老人,老人的妻子不幸受伤,老人一个人操持着家里和地里的活儿,趁着老人为妻子做午饭的空当,他们聊了很多,但老人太忙,没能完成问卷,“我们的调研既包括问卷,也包括访谈,那一次问卷没有做完,但是访谈很深入,后来我单独整理了一份访谈记录。”她说。
刘娟告诉记者,在调研中,男生们会更主动地帮助农民干活,这是他们获得农民认可最好的方式。而女生们也有自己的办法,董怡琳说,“在一个村调研时,为了更好地与村民打成一片,我们会和那些阿姨、奶奶聊她们的抖音作品。很多女性会用抖音记录自己的歌曲、舞蹈,甚至是模仿秀。通过浏览她们的作品,交流她们感兴趣的娱乐活动,很快就能拉近与她们的距离,从而开展一段顺利的问卷调查。”
在乡村里认识真正的农民
从2021年5月到2021年6月,入村入户的调研,前后经历了两个月左右,其间,四十多位老师和学生,分别在五省不同的地方,访谈了将近六百人,每个访谈对象,至少要进行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访谈,而最长的访谈可以达到三天。
天南地北的农民,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村庄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刘娟告诉记者,农民们更愿意用一种感性的、体验式的方法,表达他们对村庄,对未来的观感和想法。“他们的表达,通常没有很多想象的内容,想法常常和自身的经历有关,比如我们在一个村访谈时,他们的隔壁村,就是一个重点村,建设得很好,他们觉得乡村振兴,应该就是那个样子的,但他们又明白,自己不是重点村,很难得到同样的资源和扶持,所以也常常有人会自己安慰自己,说别人做的,都是表面文章,不符合乡村的实际。”
每天访谈之后,回到住处的师生们,会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所见所闻,讨论各自访谈的内容,以此互相启发和佐证,“个人的表达,角度往往会比较单一,综合起来,才更有可能得到事情的全貌,”刘娟说,“这样的交流有时会很久,但必须要有,学生们会把自己当天最有感触的事情,用一两句话概括,写在纸条上,然后贴在墙上,大家一起讨论。”

每天访谈之后,回到住处的师生们,会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所见所闻,讨论各自访谈的内容 。受访者供图
在一张张小纸条上,调研的学生和老师们,留下了一个个让他们感触的瞬间。“我访谈的第一个村民,是一位村干部,访谈中谈到集体负债的问题,他告诉我,过去为了发展村里,村集体负债发展种植业,种的果树好几年没有收益,刚刚挂果时,却遇到了一场冰雹。没有收入,但流转农民土地的流转费,雇人管理的费用却不能少,压力特别大。”

在一张张小纸条上,调研的师生们,留下了一个个让他们感触的瞬间。受访者供图
在另一个村庄,和一位留守妇女的访谈中,刘娟遇到了一个相似的话题,那位留守妇女告诉她,“村里的活儿,过去村长甚至是小组长喊一声,大家就主动去干了,没人会谈钱,但现在,无论是村庄的整理,还是集体产业的管理,都需要花钱雇人,没人会免费干了。”这些素材,最终成为了刘娟他们调查乡村雇工的材料,“乡村中,包括集体工作、红白喜事等,过去的互助正在逐渐演变成雇工,过去认为这是习惯的改变,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农民并不认为自己是乡村发展的主体,这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农民心中超出想象的想法
当一个个心灵深处的真实想法展现在调研者的面前时,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经受着现实世界的洗礼。
陈诺告诉记者,调研的问卷中,有一个问题,“你怎么理解生活富裕”,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不需要“翻译”成农民的语言,而且,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憧憬和答案。陈诺曾经觉得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就是要有更多的钱,“但调研中,我们发现,不是我们预想的那样,只有一少部分人认为生活富裕意味着更多的钱。大部分农民,则有一种超出我们想象的、朴素的富裕观,他们认为没有生病、没有负债,就是生活富裕。”这也从侧面反映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中医疗还是首要的,因为“许多农民家庭负债,往往也是因为沉重的医疗负担。”陈诺说。
两个月中,张森访谈了许多返乡的年轻人,他们有村干部、有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一位从深圳回乡,在村里发展生态水稻的年轻人让他记忆深刻,那个年轻人原本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做经理,发展不错,后来回乡创业,流转了村民的土地,种植生态水稻。“这些回乡的年轻人,他们见过外面的大世界,也有足够的经验和眼力,当他们发现了村里的机会时,充满希望地回到村里,现实却远不如他们想象的美好。”张森告诉记者,那个年轻人在外打工时,孩子留在村里,他本以为回来后可以和家人一起生活,但等他回来了,孩子却又因上学择校进入县城,家人也在城里陪读,还是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事实上,他自己的产业,也有许多发展的困难,“他种植生态水稻,又把他父亲的手工榨油房经营了起来,但他发现这些产品要进入正规的大市场,比他想象的要难很多。”
在一个调研村,一位中科院毕业的返乡硕士,在老家租地种植苹果,而原本在村里的农民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回来种地,董怡琳告诉记者,我们在村里的时候,有农民跟我说,“我们不好意思问他,你能不能帮我们问问他,为啥要回来种地。”
不理解年轻人回乡的目的,是大部分农民普遍的认识,张森告诉记者,“很多农民都认为乡村振兴需要人,但他们绝不愿意自己在外的孩子和家人回乡。一位年轻的母亲,原本在外打工,后来辞职回乡,陪孩子读书,她告诉我,她的压力很大,有经济的压力,也有教育的压力,她最希望的,是孩子能够真正走出大山,但她自己又没有能力辅导孩子。”
乡村的巨变中,人也在快速变化
在真实的乡村中生活,书本上的理论一天天变得鲜活,但调研的师生们,得到更多的,是书中没有的东西。
“在一个村调研时,我们住在村委会,我们发现,到了晚上,尤其是节假日的晚上,村委会一层的台阶上闪着星星点点的亮光,很多孩子聚集在那儿,一人手里一个手机,在那儿玩游戏,因为村委会有无线网,所以他们都去那里。我们其实早就知道许多孩子沉溺于游戏中,有中小学老师告诉我们,手机就是学生的半条命,但只有真正看到了,才知道那种景象是怎样的。”刘娟说。
乡村振兴的大时代中,乡村在变,生活在乡村的人也在变,而进入乡村,了解乡村的人,也同样在被乡村改变。
“调研不仅是学习怎么做一个科研项目,”董怡琳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乡村的那些真实经历,让我们知道,真正理解乡村、理解农民,理解乡村振兴,不是在城市里的研究和学习可以做到的。比如对于乡村振兴的未来,在我们的调研中,老人的信心是最低的,但同时,他们对现状的满意度又是最高的,这种矛盾的心态,如果不是长时间在乡村,如果不能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过去的经历、现在的状态,是很难理解的。”
到乡村去,对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来说,不仅是一次调研,他们在乡村,要做的事情也远超出课题之外,“我们不希望只是把乡村变成一个获取信息和数据的地方,而在努力和乡村建立起更为长久和稳定的连接,所以我们团队和我们学院也深耕于全国多地乡村,长期开展行动实践,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和教育,才能真正融入到乡村中,也更加深入到乡村振兴的实践当中,因为只有在乡村,只有和他们一起,才能知道他们真正想要什么,真正想说什么。”刘娟说。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唐峥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