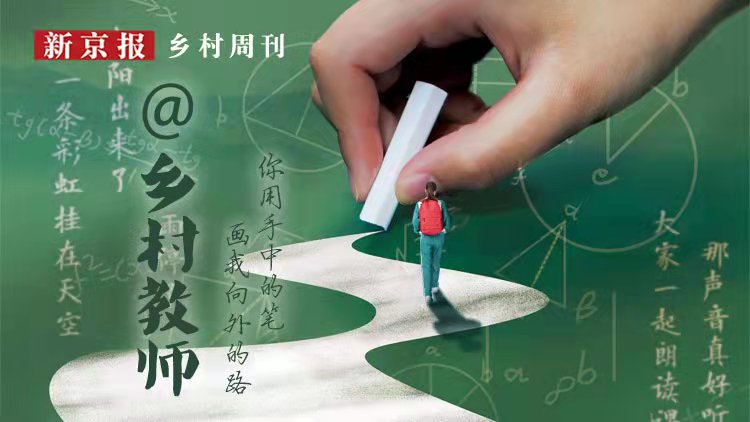新学期,原四年级二班的学生,一起进入了五年级二班的教室,他们发现语文老师还是宋学翠。宋学翠在临沂市郯城县一中教了20多年语文,今年是第二年留在花园镇涝沟小学支教,“喜欢这里的水杉树和孩子们,所以就主动留下了”。

9月7日,涝沟小学,宋学翠在和学生们在一起。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老师还在:自己带着更放心
今年6月,郯城县花园镇涝沟社区刘湖村因“一巷九博士”走红网络,在这座人口不足500户的村里,陆续走出16名博士、50多名硕士,一度引起上亿话题阅读量。涝沟小学校长张斌介绍,涝沟小学共有745名学生,来自刘湖村的学生有160余名。宋学翠说,在五年级二班,“学霸村”的学生占到三分之一。
从外面看,涝沟小学丝毫不起眼,学校在村路下方,低矮的铁丝校门有些生锈,木牌上的校名已看不全。但吸引宋学翠的是,推开校门后,映入眼帘的两排水杉树,它们将幽静从门口一路探到教学楼前。“这座学校很有底蕴,像这些树,都已经几十年了,走在下面,让人感觉很舒适很自由。”

9月7日,涝沟小学校门口。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支教老师的周期是一年,宋学翠在完成一年支教后,主动申请继续留下来,“去年带的四年级二班,这学期一开学,我们就是五年级二班了。他们都很乖,把他们丢下,真的不放心。”宋学翠今年52岁了,她曾带过多年高中毕业班,现在来到乡村小学里,感到由衷轻松,“而且我们班里的学生,整体素质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要好好学习,他们都挺省心的。家长们也特别配合老师工作。在这里,还没出现过特别闹心的事儿。”
一个瘦小的男生看起来很腼腆,在不远处瞧着宋学翠说话,被宋学翠叫到身边,“别看他在外人面前挺老实,在上学期的时候,老爱接老师话茬儿,平时还有口头语。”宋学翠轻拍了下男生的胳膊,“但是他学习成绩很好,记东西也快,就是小毛病有点多。不过也没事,孩子慢慢长大,会变得更好的。”
有几个女生围了过来,宋学翠笑着将一个女生搂在胳膊弯里,“孩子们和父母接触的不多,一般爸爸在外地挣钱,妈妈在家一边上班一边看孩子。班里还有一些同学只跟着爷爷奶奶住,这样孩子就成留守儿童了。”
十二点,大人们一般在吃午饭或午睡,却是孩子们快乐的时光。水杉树下,成群的孩子做游戏,一个一年级的学生,蹲在草丛边看蜗牛看得出神,不时发出惊奇声。拿着扫帚的六年级学生告诉记者,在家吃完饭就来学校了,在学校有人玩。“乡村的孩子,比较活泼,也比较可爱。我觉得孩子们要是能和城里孩子,有同样的师资、教学设施等条件,成绩不会比城里孩子差。”宋学翠有一点体会,乡村孩子的书写不太好,所以她平时会着重强调学生们要写好字。
学生爱学:主要靠内驱力和自觉性
涝沟小学是上午十一点二十分放学,下午一点半正式上课,在十二点四十分到下午一点半之间,是学生们自愿写字的时间。“开学刚不久,一些孩子的状态,还没完全从暑假中脱离出来,玩心未退。但大部分孩子,都已经进入学习状态了。”张斌告诉记者,有一多半孩子会自愿来校写字。

9月7日,中午十二点,涝沟小学许多学生在水杉树下做游戏。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一个五年级学生告诉记者,自己将来不打算留在村里,考上大学后,要进城生活。“学习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出路。考试是最公平的竞争了。”一位接送学生的家长说。
张斌介绍,对于小学教育来说,养成教育是最重要的,在小学阶段拥有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比一味地强调成绩更重要,他教五年级的思想品德课,时常拿“学霸村”走出来的博士举例,“有一次,带着一些学生去博士巷参观,让他们看看榜样的成长历程,再给他们讲读书的重要性,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
下午一点,教室里的学生有一半多了,校门口还有许多学生涌入,送学生上学的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将电动三轮车停放在路边,挥手向转身进校门的孩子道别,原本不宽的街道,变得有些拥堵。“我们村的学生,学习主动性很强。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我们布置作业就比较少,现在一二年级没有作业了,一些孩子会主动看书。其他年级布置一些作业,有些孩子就会选择在学校里完成。”
刘浩斌的二儿子今年从涝沟小学毕业,收到了博雅、育才等多个县重点初中的入学邀请。刘浩斌告诉记者,自己在上海务工20多年,回家时间很少,平时孩子由母亲照看,“他平时学习非常主动,大人很少管他。可能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小时候就爱学习,当时要不是家穷,就考上大学了。”
宋学翠认为,乡村小学的学生们,潜力比城里学生大,“村里没有辅导班、特长班等,他们小时候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比较小。很多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督促。农村学生要学习好,凭借的是真正的内驱力和自觉性。”宋学翠还是希望,父母尽量在小学阶段陪在孩子身边,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
乡村学校:生源流失、师资薄弱
花园镇初级中学是镇上唯一的中学,全校共有学生1450人,今年初一年级招了近430人,而全镇小学毕业人数达到867人。“从花园镇来看,有一多半农村学生,尤其是农村优质生源,不在镇里上初中了,他们选择进城读中学。”花园镇初级中学校长徐军厚告诉记者,随着城镇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生源明显在向城里流动。

9月7日,花园镇初级中学的操场。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但乡镇中学生源减少不一定全是坏事,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师生比会变高,单个学生能获得老师更多的精力。一个老师教80个学生,和一个老师教60个学生,教学效果是不一样的。”徐军厚说,在城乡之间教学硬件设施差距日渐缩小的今天,生源减少会使得个体学生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
花园镇初中有看起来很新的教学楼、餐厅和学生公寓,但操场是一片约30亩的野地,中间长满了野草,一下雨,四周的土路变得泥泞。“虽然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在这几年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在一些设施上,仍和城里学校存在不小差距。”徐军厚说。
师资薄弱是乡村教育显而易见的短板,即使是校长,徐军厚要兼职生物老师,张斌兼任思想品德老师。涝沟小学共有教师40名,支教教师占9名,花园镇初中有103个老师,支教老师有25名。

9月7日,涝沟小学,校长张斌在办公室。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在艺术教育方面,花园镇初中仅有一名美术老师和一名音乐老师,碰到老师请假的情况,一些美术和音乐课,由其他老师兼任。“这是乡村学校的一个困境,不仅师资数量薄弱,而且在美育等特长教育方面,缺少专业人才。”徐军厚介绍,现在国家实行“教师轮岗”等促进教师流动的方式,已经有力缓解了乡村教师数量的不足。
目前,花园镇初中的课后服务是从下午五点二十分到六点十五分,以后可能还会再加自习课,一直延长到七点。徐军厚家在县城,离学校28公里,他每天早晨五点来学校,晚上十点到家,“但课后服务,对学生、家长来说是一件好事。一般情况下,孩子放学时间比家长下班时间要早,这就形成一个孩子无人监护的空窗期,课后服务实行起来了,学校就承担了更多监护学生的责任。”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