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堂吉诃德沉思录》中译本出版之际,奥尔特加研究者、西班牙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思想史教授哈维尔·萨摩拉·波尼亚(Javier Zamora Bonilla)撰写书评。他主编有《奥尔特加全集》等书。本文为独家首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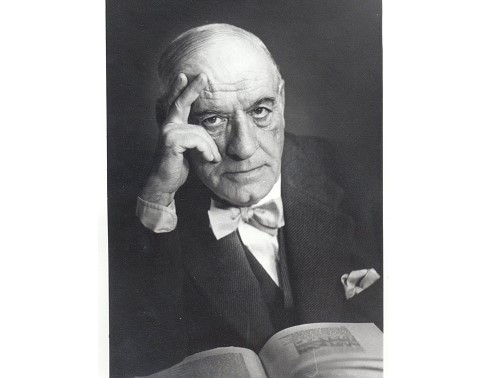
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20世纪西班牙哲学家、思想家、文艺批评家、随笔作家。代表作有《大众的反叛》《堂吉诃德沉思录》《艺术的去人性化》等。
撰文|[西班牙]哈维尔·萨摩拉·波尼亚
翻译|蔡潇洁

《堂吉诃德沉思录》,[西班牙]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 著,王军、蔡潇洁 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4月。
在新旧世纪之交诊断欧洲现代文化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堂吉诃德沉思录》于1914年7月末问世。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几天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于奥尔特加来说,一战是从几十年前就开始的西方危机的症候,而非原因。在他看来,“大战”,按照当时人们的说法,对当时的所有领域都意味根本性的剧变:政治、经济、文化、人们理解生命的方式等。
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这位20世纪西班牙最知名的思想家对这场自19世纪末即初露端倪,被法国人称为“世纪末”危机的西方文化危机的起因进行了勾勒。在哲学视野下,弗里德里希·尼采是这段被西方社会和科学文化理念质疑的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称“那是一段令人惴惴不安的岁月”;奥地利诗人胡戈·冯·霍夫曼史塔说“那是一段前途未卜的日子”;而同为奥地利人的斯蒂芬·茨威格则坦言它终结了“昨日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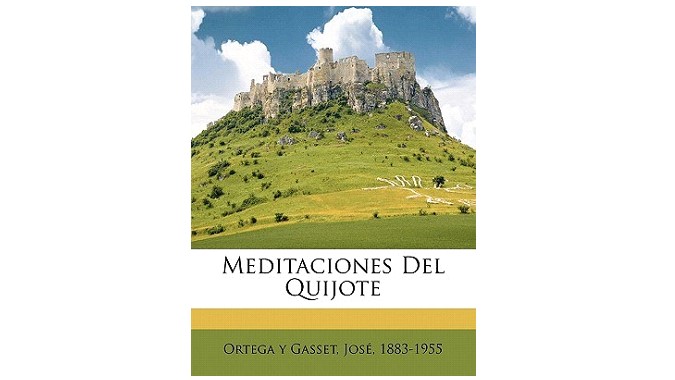
《堂吉诃德沉思录》(Meditaciones del Quijote)西语书封。
奥尔特加认为,欧洲现代文化从15世纪以来以科学为主要特征,但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在理解人的因素方面存在不足,无法理解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无法认识每一个“我”在其所处的“环境”,在他的世界中具有的意义,也无法回应现代性本身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如所谓的“社会弊端”和无产阶级恶劣的生存状况,这种状况是在工业快速转型和从农业社会到第三产业和大城市激增的大众社会过渡过程中产生的。我们这个世界,对于很多已经不再赞同欧洲理性主义现代性“信条”的知识分子们而言,已经出了问题。
奥尔特加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提出,需要将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欧洲北部理性主义文化与基于印象与感觉的地中海文化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唯一的欧洲文化。奥尔特加通过塞万提斯的伟大作品《堂吉诃德》,以象征性的方式提出了西班牙对促成整体性的西方文化可以做出的贡献。在所谓的“塞万提斯模式”,在如何看待现实,如何“接近事物”的“塞万提斯方法”中,奥尔特加找到了一种比笛卡尔和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所提倡的科学方式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理解生命。
所有人,不仅具有生命,而且是历史性的
在《我们时代的主题》(1923)等若干部后来发表的作品中,奥尔特加认为应当要超越哲学的唯心主义,并提出了不同于抽象的理性主义的生命理性。所有人,不仅具有生命,而且是历史性的,生命理性就是从这个基础上阐发的。
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奥尔特加通过解读塞万提斯,发现了一种人类学,可以理解处于不同环境中的每一个体。真正的英雄气质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的疯狂游侠骑士出门寻找冒险,而是在于每一个人对自己的道路的坚持。生命中处处有“十字路口”,每一个个体都需要在岔路口做出自己的选择。堂吉诃德有很多次都让他的那匹瘦马驽骍难得随便选一条路,因为他觉得在任何地方都能建功立业。奥尔特加建议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个体都握住自己命运的缰绳,走自己想走的路,发挥自己真正的天赋,并且坚定地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尽管我们可能永远也到无法到达巅峰。奥尔特加非常塞万提斯式地说:“旅途要好过客栈,生命的过程比抵达一个家一般安稳的所在更加重要。”

电影版《堂吉诃德》(1957)剧照。
堂吉诃德因为阅读希腊诗歌中记载的史诗、欧洲古老谣曲和骑士小说而变得痴狂,史诗歌颂的是活在传奇世界中的超级英雄所具有的不合时宜又神秘莫测的英雄气质,然而塞万提斯的小说将我们置于一个生命的历程中,尽管以抒情和想象的方式呈现,但呈现给我们的仍然是现实,是与人有关的事情。塞万提斯将人性赋予他笔下的人物。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失败的英雄,经受了一个又一个挫败,但始终没有抛弃初心,或者说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放弃的。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那个追随他的主人,且大多时候比主人公更抢眼的可怜农民,都让我们觉得很真实,因为他们的游历表达着他们所处时代的生命问题,同时也就是人类的问题:生命、爱情、基本的需求、家庭关系、对财富的渴望、社会实现、信仰或者失去信仰、与他人的关系、社会期待与碰壁、时代的信仰等等。
在《堂吉诃德沉思录》的“第一思”里,奥尔特加从塞万提斯的杰作出发,写了一段“小说简述”,《堂吉诃德》作为不同于史诗文学的第一部现代小说,赋予文学以人性,用一种迟缓、诙谐的方式描述人的故事,把书中的人物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英雄。
奥尔特加年轻时曾在德国马尔堡大学就读两年,他和他的老师——犹太人赫尔曼·科恩一直就《堂吉诃德》这本书保持着重要的对话。科恩在他的著作《纯粹意志的伦理学》里发问:“《堂吉诃德》只是一出闹剧吗?” 奥尔特加把这句话用在自己的书的开头,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明确:不,《堂吉诃德》不仅是一部逗乐小说,不仅是对骑士小说和中世纪骑士理想的戏仿,不仅是第一部现代小说和世界文学的伟大巅峰之一,它还包含着一种人类学,一种理解人性的方式。人们不再轻易被笛卡尔在同一时代的欧洲中心所提出的理性主义方法所俘获。要理解人性,理解人类在世界上行为的方式,要与人交往,很多时候都需要反讽和幽默感、同理心,尤其还有悲悯之心。科学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人的一些事情,关于人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但是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人。关于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基于生命理性的哲学可以回答。

上世纪50年代,奥尔特加与海德格尔。
在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中去理解他
《堂吉诃德沉思录》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奥尔特加的哲学思想,那就是“我就是我与我所处的环境,如果我不能拯救我的环境,自己也无法得救。”意思是说,欲理解每一个人,理解自己,就要将我们每个人周围的世界,将我们所处的环境考虑在内,这里的环境是物理的(比如地区),也是精神的(比如文化)。用奥尔特加的话说,应该在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中去理解他,无论是物理环境还是精神环境。在他后来的哲学表述中,又提到“我的生命是根本性的现实”,即是说,在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其他的现实,它们是我与环境的结合体。西方哲学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执着地追寻存在的本质,与巴门尼德认为存在的本质变居不动不同,奥尔特加认为根本性的现实,即我的生命,是一种具有依赖性的存在,“我”既需要“环境”,“环境”也需要“我”。
另外,生命并不是静止的、永恒不变的存在,相反,它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不会绝对完成和终结,直到死亡的那一刻,而死亡已经不是生命的一部分了。事实上,生命不是“存在”,而是“存在着”,永远是“未完成”的状态。在任何时候,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要决定自己生命的未来,尽管那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微小的决定:我们的生命将一如既往。生命,永远从过去而来(个人和集体的过去),并去往未来。
在另一篇文章同样发表于1914年,和《堂吉诃德沉思录》时间相近的文章《作为序言的美学小论》中,奥尔特加提出了“行为的我”这一概念。不同于西方唯心主义中“意识的我”,不同于康德所认为的“我”将世界看作现象和反映,无法接近事物的终极现实,即本体;奥尔特加认为哲学应当从生命的我出发,这里的“我”就是我们所说的“我在走路,我想要,我厌恶,我感到疼痛”的“我”,一个活着的“我”,在这个生命中,我“验证着、存在着和行动着”。不是理念的爱,而是充满激情的活着:这就是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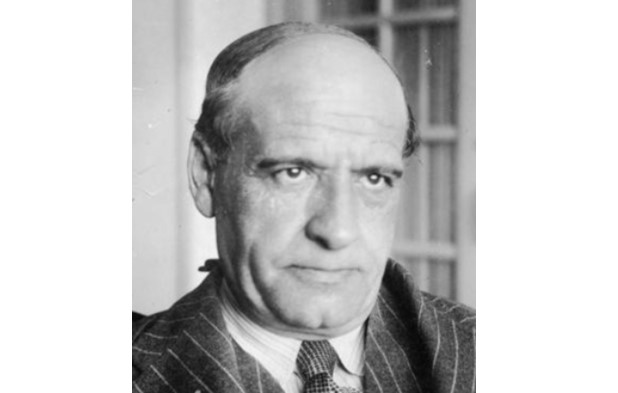
奥尔特加鼓励每个人善待自己的出生之地。
奥尔特加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拯救”自己的环境,即是说,努力使环境得到完满形式的发展。前面引用的“我就是我与我所处的环境,如果我不能拯救我的环境,自己也无法得救”这句话是奥尔特加对一句拉丁语表述的扩展,他借此鼓励每个人善待自己的出生之地。每个人都应该试着使自己出生并且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变得更好,通过这种方式,他也可以“拯救”“我”,即他自己的生命。奥尔特加说“对环境的重新吸纳决定了一个人的具体命运”。我们应该重新吸纳我们的环境,吸收它,将它内化,这样我们才能使自己得到发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环境中被动采取行动,相反,因为环境中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困难,我们就要利用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来应对困难,把困难变成新的可能性,开阔我们生命的地平线,拓展我们的命运。
奥尔特加在《堂吉诃德沉思录》里把他们那一代人称为“爱国、美学和科学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否认自己那个时代的西班牙,对继承到的遗产持十分批判的态度,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感到自己有责任去建设一个新的西班牙。
“视角理论”和“隐喻的传授法”
在《堂吉诃德沉思录》这本书里我们还能发现另一个特点,它也是定义奥尔特加全部作品所表达的哲学思想的若干特性之一:那就是视角理论。
奥尔特加认为,我们只有综合不同的视角,才能逐渐地认识到现实的真相。人不可能获得认识现实的绝对全面的、所有角度的视角,他只能部分地认识现实,而这部分已知的现实也是现实的一部分。为了阐释这一理论,奥尔特加用安葬西班牙多位国王的埃斯科里亚尔皇宫修道院周围的铁艺林打比方。我们的哲学家问,要多少棵树才算一片树林。一个身在林中的人是看不见树林的,他只能看见自己周围数目有限的树,那么它们是树林吗?这就是表层现实,它暴露在我们的感官之下,我们可以动用视觉、嗅觉、触觉、听觉捕捉到。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深层现实,它不能被简单地看到,我们无法用感官直接获取,而只能通过概念来了解。“树林”这个概念所表达的并不是我们置身其中的那个现实,而是我们直觉知道存在于那个浅近的现实后面的现实。我们只有从这个高度视角,而不是在林子里面,才能看到整个树林。因此,我们对现实的获取总是从某个视角出发的,一个我们自己的视角。而如果想要理解全部现实,或者大部分的现实,那就只有一种方法:增加视角,把自己的和别人的视角汇集起来。

奥尔特加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失去联系即意味着幻灭”。
奥尔特加习惯带着一个橘子或一只苹果进课堂,把它放在讲台上,向他的学生们解释视角理论。他问学生们有谁曾经看到过一个橘子或者一只苹果。当有人举手,说自己曾经看到过,奥尔特加就会向他解释说,实际上,我们从来不能只凭一眼就看到一只苹果,因为这个苹果总会有某一部分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其他的感官也面临同样的状况。我们所看不到的那一部分苹果是隐蔽的,我们根据以往对于苹果认知的经验,直觉认为它存在,但是那一部分的苹果可能已经被人切掉了,因而并没有一个苹果,而是只有半个。
另外,苹果也有深度,它的内部是我们无法直接看到的。我们得把苹果切成薄片才能逐渐看到它的内部,但是即便切片再薄,也终究具有一定的厚度,我们的感觉无法完全地触及,除非我们使用显微镜,但是从显微镜看到的也不是苹果,而是苹果的微观部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深层维度。概念,作为苏格拉底的伟大发明,帮助我们把一样事物与其他事物、一个现实与其他现实区分开来,而在区分的同时,也在它们之间建立了联系。
视角主义寻求多种视角的整合和事物的联系,因为现实总是通过某种视角得以呈现。奥尔特加认为“失去联系即意味着幻灭”。世界是联系的。奥尔特加的哲学论述方式是对“理智的爱”的热情实践,“理智的爱”是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表述。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在评价奥尔特加的作品时说,奥尔特加的哲学是爱的哲学,它寻求事物之间的连接,以此来认识现实。现实就在那里,但是我们只能逐渐地认识它,逐渐掀开覆盖其上的面纱。这就是古希腊哲学中真理(alétheia)的概念,意思是“揭示”。
奥尔特加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谈到了“隐喻的传授法”。他认为如果有人想要向我们教授真理,最好的方法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引导我们走上发现真理的道路,使我们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知识的增长到达真理。我们要靠自己走这条路。这是真正的哲学方法论,即打开通往终点、通往知识港湾的道路。哲学,对智慧的爱,始于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感到惊奇的时候(希腊人把智慧女神雅典娜比喻成一只圆睁着惊奇的大眼睛的猫头鹰)。正是从那惊奇和困惑中,人们在现实的知识之路上前行,逐渐揭示真理,抵达真理。奥尔特加在另外一些场合里也将这种方法称为“熏陶法”,他说,老师应该传授给学生的最重要的东西,哲学,也就是对智慧的爱,其实是无法教授的,他只能以身作则,通过自己所表现出的对哲学活动的热爱感染学生,使他们看到,并且走上老师为他们打开的道路。
作为第一阶段哲学思想高峰的《堂吉诃德沉思录》

电影版《堂吉诃德》(1957)剧照。
《堂吉诃德沉思录》是奥尔特加第一阶段哲学思想的高峰。新康德主义哲学和现象学先后对他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海量阅读西方文化,尤其是他所处时代西班牙的文学和思想也对他影响至深。《堂吉诃德沉思录》有一种紧凑的对话感,有时并不十分明显,对话的对象不只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塞万提斯,还有一些与奥尔特加同时代的作家,比如弗朗西斯科·吉纳·德洛斯·里奧斯、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拉米罗·德·马埃斯图(《堂吉诃德沉思录》就是献给他的)、皮奥·巴罗哈和阿左林。
奥尔特加的哲学思想是试图回应20世纪重大哲学问题的最有深度的哲学之一,而《堂吉诃德沉思录》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第一个重大成果。这种思想被称为生命和历史理性哲学,因为它从作为根本性现实的生命出发,并意识到生命总是具有历史性的。“人没有天性……而只有历史”,奥尔特加很久之后说道。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稍作修饰,说成“人几乎没有天性”,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的天性固然重要,但是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文化和历史则更加重要得多,因为人类始终是过往的继承者,他们在续写一份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记载的人类大传记的同时,还试图遵循着各自的天赋,构建自己的生活。
生命和历史理性系列思想也在奥尔特加后来的作品中得到阐释,如《我们时代的主题》(1923),《哲学是什么?》(1957),《思想和信念》(1939),《作为体系的历史》(1941)或《关于伽利略》(1947)。关于这个系列,或许现在不是深入论述的时候,所以我们只是略微提及(作为自由的生命、作为宿命的生命、作为任务、未来、戏剧、信仰和传承的生命等等),通过这些哲学思想,我们最终可以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思索,并且应对那些全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未来的成功就蕴藏在对现实的准确理解之中。
文中部分黑白照来自http://www.libertas.co网站。封面题图为电影版《堂吉诃德》(1957)剧照。
作者 | [西班牙]哈维尔·萨摩拉·波尼亚
译者 | 蔡潇洁
编辑 | 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 | 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