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则网传“某厂23岁员工加班后猝死”的消息刷屏社交媒体,再次引发公众关于“996”“过劳死”的讨论。根据网友爆料,该名员工生前从事买菜工作,1998年出生,年仅23岁。1月4日,出事方发布公开声明称,北京时间12月29日凌晨1 : 30,某张姓员工与同事一起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厥倒地,后送往医院急救无效,不幸离世。
过去两年,类似的新闻与讨论并不少见。在996遍地走的今天,工作日加班,节假日加班已经成为了常态。“过劳”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底色。
2018年,我们曾就“过劳”问题采访过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教授。他是中国最早研究过劳问题的学者之一,长期研究中国过劳问题的根源以及对策。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旧文重发,希望借此与更多读者一起思考“过劳”现象背后的工作困境与可行的解决方案。
采写 | 徐悦东

杨河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
“如果让欧洲人加班,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让美国人加班,必须认真的给他讲清楚加班补贴和调休等相关政策,他才有加班的可能;如果让中国人加班,有加班补助就早已感激涕零。”
这是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加班段子。在中国,不仅企业的管理层、白领、底层蓝领经常加班,连在很多人眼里悠闲的公务员也不能幸免。而且,很多企业连加班费都不能保证。据《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九成行业周劳动工时超过40小时,住宿、餐饮业周平均劳动工时长达51.4小时,位居第一;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及其他服务业位居二到四位,以上行业均超过《劳动法》规定的“特殊行业”49小时工时上限。
而根据2015年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的课题组全国抽样所做的调查,2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小时及以下,27.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1-48小时,26.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9-59小时,18.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0个小时及以上。而加班原因的前三位分别是“人手不够,工作量大”(30.7%)、“工作内容和目标有变更”(17.6%)、“递交任务期限短”(16.3%)。在问及加班工资时,56.5%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没有支付补贴,24.5%的人认为企业只支付了部分补贴,完全支付的仅占15.5%。
杨河清课题组按照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的标准,对北京的白领进行预警分析发现,有61.6%的人已经进入了“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而处于“红灯”危险区,即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的人,占据26.7%。形势十分严峻。
中国的过劳现象十分普遍,但是学术界却关注得很少
新京报:《过劳时代》受到了日本读者广泛而持续的瞩目,在日本一版再版。中国的过劳现象也非常严重,但是这个议题在中国被很少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我国没能像日本一样,引起广泛讨论和关注呢?
杨河清:日本舆论对过劳问题的关注的确比中国多。这是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过劳问题就非常严重。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工作时长是最长的。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那么快,跟劳动者不遗余力地付出是有关系的。但是过劳也危及生命,有损家庭幸福。所以在那时,有一批学者、律师和过劳死者的家属,创立了一些组织,向社会呼吁预防过劳死,这引起了很大反响。
相比之下,中国很晚才开始关注过劳问题。当然,近几年来,我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也越来越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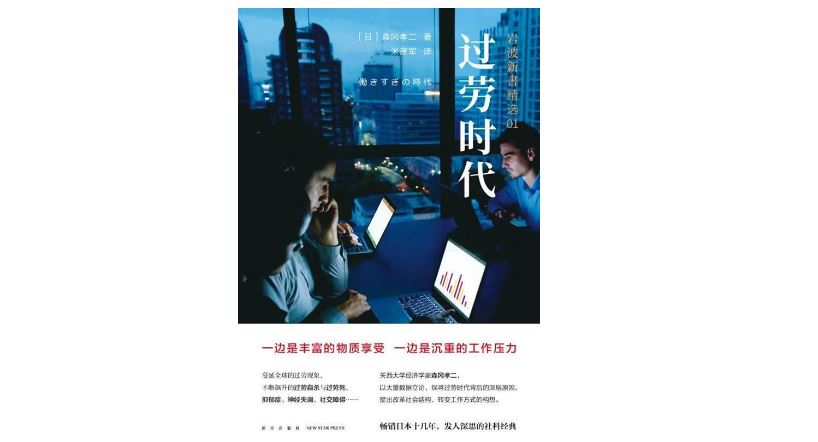
《过劳时代》,森冈孝二 著,米彦军 译,新星出版社 | 新经典·岩波新书精选,2019年1月。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过劳问题的?中国过劳研究的发展情况如何?
杨河清:在2007年,因为一个契机,我开始关注过劳问题。我在飞机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一个韩国的媒体在2006年,报道说中国每年有六十万人过劳死,这个新闻当时被《环球时报》转载了。我作为学者,我的思维方式是批判性的。每年六十万人过劳死,韩国人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劳动经济学和劳动关系是我研究的领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有任何一个学者或者机构,和韩国合作研究中国的过劳死问题,或者有中国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告诉过韩国人。客观上中国也许每年都有很多人过劳死,但是在那时,中国的过劳死研究几乎一片空白。韩国人单独对中国进行研究不太好吧。
因为中国没有关于过劳死的法律依据和标准,那韩国人是依据什么标准对中国的过劳死进行判定?中韩两国国情不同,用韩国的标准显然不行。从这两点出发,我认为这个报道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2007年,我组建了研究团队来研究过劳问题。我们发现,在2007年以前,只有媒体上有一些零散的过劳死报道。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会抱怨工作很疲劳。但只有个别中国学者零星地翻译过一些相关研究报告。探讨过中国过劳问题的不到十个人,很多人也就发表了一篇论文。所以我要研究和发声。我后来也接受媒体采访。因为媒体可以影响更多人,让更多地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
在2012年,为了让研究过劳问题学者更好地交流,我建立了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中心,每年以研讨会的方式,去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也经常被日本和韩国邀请去开研讨会。我们的研究跟他们的差距很大。因为我们的研究还是非常初级的,而他们已经深入到了各个学科。过劳问题是很多日本学者一辈子在研究的课题,而不是随便翻译几篇文章说几句话就可以的。

《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的工作时间》,赖德胜、孟大虎 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
新京报:为什么中国会那么晚才关注到过劳问题呢?
杨河清: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关注的主流都是怎么去发展,比如经济增长、就业、工资、效率的问题。在经济落后的状态下,强调这些是没问题的。而过劳是属于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问题,这个得往后放一放。
而现在,大家普遍更关注民生问题。这里面也包括了健康问题。所以大家普遍关心食品安全和空气污染。职场环境和文化也关乎我们的健康。现在大家逐渐开始谈到这些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会有一些学者把视角转向研究过劳这种“非主流”的问题。
新京报:你刚才也提到,对中国过劳的测量和界定的标准需要本土化,那么该怎么本土化呢?现在在学术上有没有一个准备要出来的标准?
杨河清: 这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去设定这个标准,最后进入立法。这是我们远期的愿景,离实现还太远。我们前期调研的工作还正在做,包括过劳的现状、群体、程度、原因和后果。假如想在现有的法律下,再增加预防过劳的条款,我觉得至少还需要十年。
而日本的标准建立得很好。2015年,日本安倍政府做了一个决定:日本每年都要发布过劳方面的白皮书。另外,在医学上,他们关于过劳死的鉴定标准是很健全的。所以,假如有人过劳猝死了,是可以诉诸法律的。
他们还解决了过劳抑郁这种疾病的判定标准。因为导致抑郁的原因有很多,所以这就要有医学上的研究了。还有,他们还解决了过劳自杀的判定标准。但是在中国,很多领域的学者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资源放在这个问题上面。当然,国情不一样,我们也不可能直接把日本的标准照搬过来用。
新京报:可在大家的印象里面,日本经济在九十年代停滞之后,现在日本年轻人似乎在流行“小确幸”、御宅族和啃老族,感觉他们不再把努力工作当成一种追求。但是在《过劳时代》书里,日本年轻人还是经常过劳的,很多人还会主动过劳,你觉得这两种现象冲突吗?
杨河清:这样的年轻人都是新生代吧。有些人还没有进入劳动市场。这一代人跟他们的父辈确实非常不一样。但目前这部分年轻人在职场的比重相对比较低。职场的中坚力量依然是七零后和六零后,甚至还包括很多五零后,因为日本的退休年龄比较晚。他们的五零后很多还是领导级别的,六零后更多是骨干级别的,压力很大。
所以,日本人所谓的过劳指的更多是这一批人。村上春树所说的“小确幸”,更多指九零后,当然也包括一些八零后。所以,未来的潮流可能是“小确幸”。年轻人有他们的标签,但是目前作为整个劳动群体来说,依然处于过劳状态。

日本社会过劳现象严重。
在目前的中国,有限度的过度劳动是我们的宿命
新京报:过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杨河清:因为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候,劳动力供不应求,在日本也是这样的。还有菲律宾人,韩国人,中国人去日本打工,跟日本人竞争。九十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经济发展速度迅速降下来了。这时,劳动力甚至会供大于求,可是为什么大家还过劳呢?这就跟职场文化和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北欧的国家,就很少有这种问题。他们很早就转向福利国家了。他们已经平衡了生活和工作。他们不会说,我一生就是为了事业奋斗,他们更愿意享受生活。但在中国,大家对事业都很有追求,大部分人还是想往上爬,在一线城市立足也是很难的。
此外,像日本人,他们做事非常精益求精,这会投入很多时间精力。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是在高端市场,反而会受消费者青睐。所以,这跟市场也有关系,虽然背后是文化的原因。这太复杂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主动过劳和被动过劳的区别?
杨河清:主动过劳的背后也是压力。你得不断为企业牺牲,才可能会被领导青睐。像大学、媒体等文化产业,可能主动过劳比较多。因为人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包括社会声望、地位和收入等。他们有这种条件去自我实现。
另外一类人就是被动过劳的。尤其是底层的蓝领工人。订单来了工人是推不掉的。若是不服从,企业可以开除你,替代的人太多了。但守法的企业应该要付加班费。
新京报:有没有办法上升雇主选择加班的成本呢?
杨河清: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雇主损害的不仅仅是员工的健康,也是国民的健康。我们得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要让大家至少有这种意识。
新京报:所以要用法律和舆论压力去增加加班的成本?
杨河清:对。这也是个道德上的事。我们毕竟才刚刚起步。在这个阶段,企业家追求利润还是第一位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对员工的关爱都退居二线。所以我们要进行呼吁。
而且,很多企业还不给加班工资。对于加班,中国法律是有规定一周最多加班多少的。而且加班工资是平时的两倍。有些国家是三倍,咱们算比较低的。很多企业并不会支付两倍的加班工资,甚至连加班的原有工资都不支付,加班就是无偿劳动了。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美] 迈克尔·布若威 著,李荣荣 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2月。“为什么工人这么努力地工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运用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揭示了工人自发的同意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新京报:所以,在中国预防过劳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杨河清:想要改变,这得随着市场的慢慢成熟,社会的发展逐步展开,发达国家也是这么慢慢过来的。企业是市场决定的,但现在的市场又不是很道德的、很成熟的,法律规范不够,竞争的残酷性都落在员工身上了。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们的研究还不够。
我们的国家还是希望能富强,正属于上升期。这会传导到基层组织,不努力可能会被淘汰。中国人均自然资源不丰富,不像挪威、加拿大、中东国家等,可以比较悠闲,就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我们的很多企业管理方式还很落后,人力资源的素质也不是很高。所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除了劳动关系的变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资源,就是要靠更长时间的劳动。
但不是无限的加班,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在突破了某个临界点之后,这个总效益是负的。在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况下,从经济学上来讲,你加班的时间越长,它的工资率上升很快,人力成本迅速上升,加班所创造出价值的边际效益迅速下降,最后会得出一个盈亏点。
而且,社会的盈亏点在企业的盈亏点上方,在这两个盈亏点之间,企业在赚钱,但是社会已经亏钱了。因为企业把它的一些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包括社保、医疗、员工健康等。
新京报:那还有什么变量会影响这两个盈亏点呢?
杨河清:这个就是我们要研究的秘密。掌握这个盈亏点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理论上说,目前在中国,有限度的过度劳动,是我们的宿命,通过有限度的过度劳动,来弥补我国其他资源上的不足。我正准备把有关这个盈亏点的研究在完善之后发表在期刊上。这个盈亏点精确在什么地方,我还说不出来。但我要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件事,你严重过劳,企业和社会全会亏损。
贫富分化和过劳之间有没有关系?
新京报:《过劳时代》里面有个观点,欧美从八十年代开始慢慢工作时间开始延长,这可能跟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施行有关。而且作者还观察到,收入越不平等的地方,工作时间越长,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杨河清:其实在八十年代,跟中国比的话,欧洲的工作时长就不算长。在欧洲,雇主也不可能严重违法,不然雇主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这也许跟在新兴国家的经济竞争有关。世界发生变化,新兴国家发展很快。很多发达国家还是要进行创新和科技产业升级,才能保持高产业链的位置,这也会传导到社会下层,也许加班也会相对增加。
新京报:你认为贫富分化与过劳之间有联系吗?在《过劳时代》里,贫富悬殊的地方加班越长,这两个变量有没有什么关系?
杨河清:也许有一定关系,但是要看情况。虽然日本是“格差社会”,“格”是阶层,“差”是差距。但是,它的基尼系数还是在发达国家中很低的,才零点二几,咱们都快接近零点五了。日本的阶层差距其实并不大,但是依然过劳。所以这就是贫富分化造成过劳的反面例子。这也许跟东亚文化有更大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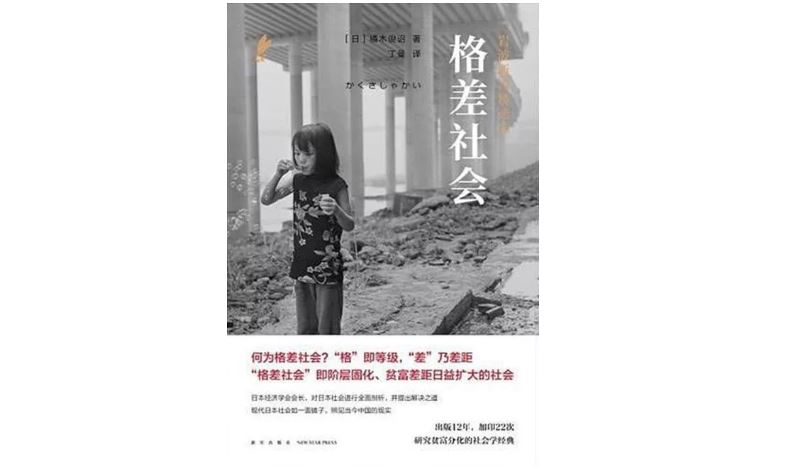
《格差社会》,橘木俊诏 著,丁曼 译,新星出版社 | 新经典·岩波新书精选,2019年1月。
新京报:但是,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贫富分化加剧,底层的人民收入变少,他们只能不断增加工作时长来增加收入?
杨河清:这你说得非常准。他们通过不断增加劳动时间来赚钱。上层的人不一定是这样的。原来老加班的上层也接着加班,原来不加班上层也很悠闲,他们形成了一种习惯。所以,很难去讲阶层差距直接造成了过劳,但是阶层差距造成了底层过劳。
新京报:假如福利增加的话,会不会减少过劳现象?
杨河清:不会。因为人还是有更高的追求,可能被迫过劳会少一点,这个得进行研究。我得一百块,就不干了,这个可能性也有,但是要看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还有能力去追求更多收入,他们得多次失败才会降低目标的。现在社会心理都很紧张,大家看待金钱的态度都不太平和。北欧就很清闲,因为他们不太考虑赚钱的事。
新京报:那可能是因为北欧的福利好吧?
杨河清:他们不在意赚钱,而我们却都在攀比。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就要比学习比才艺。至于福利制度和过劳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得做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离线权”的背后,公私分明的文化
新京报:信息革命也改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比如,电邮和微信令大家随时都能工作。法国有一项“离线权”的法案,下班后可以不回复工作电邮,你怎么看待这项预防过劳的法案?
杨河清:2004年我去英国一所大学访问,我跟他们的管理学院院长晚上一起喝啤酒。我就问他,你作为院长,假如你突然想起什么必须要通知大家的急事,你会怎么处理?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很震惊,因为就直接按他们的法律来加班就好了。一个电话打过去,就首先告诉下属,我有一个“公事”要跟你商量,并说明这是加班时间,愿不愿意加班是自愿的,愿意的话有加班工资。我们就从来没这个意识。这个意识最早是一种公私分明的文化,然后形成法律,法律执行的时间长了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所以双方都非常默契。很多社交媒体在2004年还不存在,他们这些就有了这样的文化,现在有“离线权”也不奇怪。
新京报:文化产业是需要闲暇时间去消费的,所以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不是需要减少劳动时间才能发展起来?
杨河清:你这思路很有意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理论上来说,文化产业需要时间去消费,而过劳也限制了这种消费。虽然发展文化产业不是为了减少过劳,但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和追求精神需求本身,可能有这样的派生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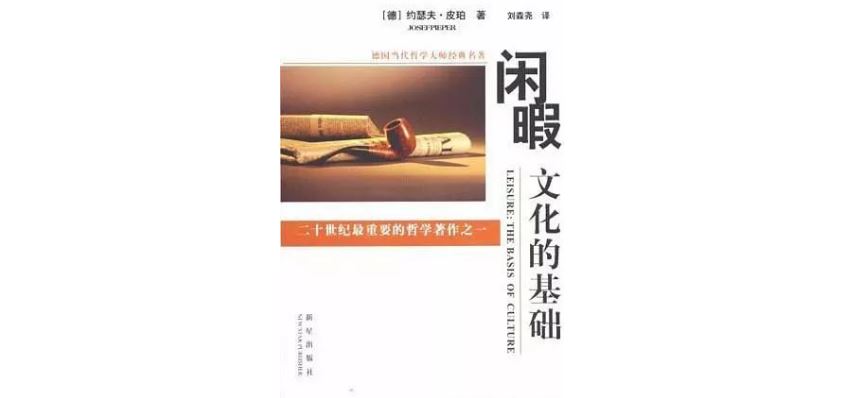
《闲暇:文化的基础》,约瑟夫・皮珀 著,刘森尧 译,三辉图书 | 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有关闲暇的哲学思考。闲暇不等同于懒惰,也不是工作的休止。它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作,具有人性的意义。
新京报:你对中国预防过劳的前景乐观吗?
杨河清:目前来看并不乐观。第一,希望我们的研究,能更多引导社会,包括政府、雇主和员工,平衡地看待工作和生活。第二,希望媒体多报道一些过劳死的案例,给大众一些警示,毕竟每个人毕竟都想长寿健康。第三,还要看我们国家发展得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尽快能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国家的期望很高,这也会把压力传导到各个下层单位组织。想要国家调整这个期望,是不太可能的。
本文原载于2018年12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封面题图为意大利剧《工作》(1961)剧照。
作者 | 徐悦东
编辑 | 安安 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