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丨何安安
1939至1940年间,沦陷时期北京的一份英文报纸《北平时事日报》(Peking Chronicle)上,连载了一部题为“小吴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Wu)的故事,通过虚构的主人公小吴的经历,生动地描述了市民的生活习俗,反响非常热烈。应读者的要求,作者很快将其修订汇编为《小吴历险记——一个北京人的生命周期》(The Adventures of Wu:the Life Cycle of a Peking Man)一书,分两卷由北平时事日报社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出版。英文版之后,很快就出版了式场隆三郎翻译的日译本。1944年,周作人读了该书的日译本,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叙述北京岁时风俗婚丧礼节,很有趣味,自绘插图亦颇脱俗”。
198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重印了该书的英文版;1988年,日本又出版了一个新译本叫作《北京风俗大全》。但一直以来,这部由老北京人书写,讲述北京人故事的汉学著作,都没有中文版出版问世。吴晓铃、葛兆光、季剑青等名家分别阅读过该书的日译本和英译本,他们都曾经呼吁对这一著作进行翻译,出版中文版。2020年8月,由罗信耀之子罗进德,耗时十余年时间翻译的该书终于得以出版问世,中译本最终被定名为《旗人风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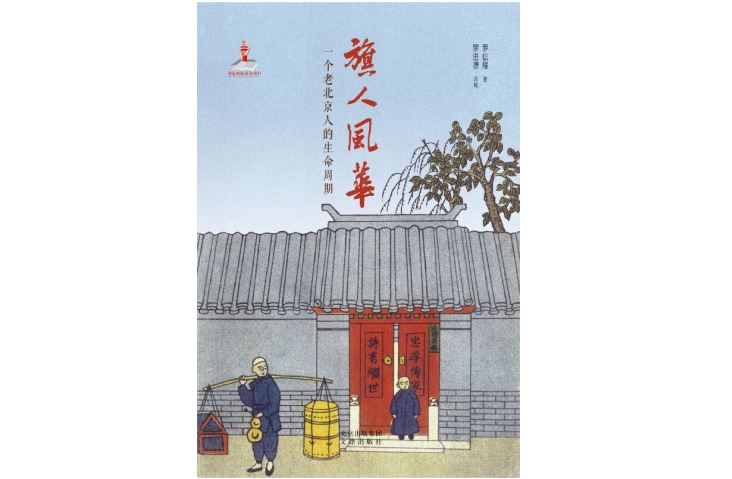
《旗人风华——一个老北京人的生命周期》,罗信耀著,罗进德译,文津出版社,2020年8月。
近日,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季剑青,青年作家、北京文化研究者侯磊以“在小说与民俗之间”为题,分别从学者和写作者的角度,对《旗人风华》进行了阅读分享。

“在小说与民俗之间——《旗人风华》阅读分享会”现场。从左到右依次为高立志、季剑青、侯磊。
《旗人风华》的时代背景是庚子事变
2015年,季剑青曾在《北京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罗信耀和他的北京旗俗书写》。在分享会现场,季剑青讲述了自己和《旗人风华》一书的渊源。他曾偶然间阅读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的英译本,在该书的导读中,著名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猜测该书的作者中文名叫卢兴源。显然,卜德在当时并不认识罗信耀,也不知道作者的情况。为此,季剑青开始考证这部著作的作者到底是谁?
后来,季剑青找到了一部日译本,书名叫《北京的市民》,书中明确了作者是罗信耀。但因为书名差异过大,一般人很难将《The Adventures of Wu》和《北京的市民》联系起来,他找了很多线索才得以确认。
在《旗人风华》出版以前,该书曾经还有一个中译本,但最终没能获得罗信耀之子罗进德的授权。这一译本源于英译本转译,虽然翻译较为准确,却没有老北京味儿。这之后,罗进德开始着手对父亲的著作进行翻译。翻译北京文化的书,怎么能没有京味儿呢?为此,罗进德查阅了大量金受申、王世襄、常人春等谈老北京风俗的书,以及《北京土语辞典》《北京梦华录》等,最终完成了译作。
季剑青发现,《旗人风华》的原著书名很有意思,如果按照中文直译,应该叫作《小吴历险记》。“历险记”是西方题材,这种写作模式会给人一种主人公面对未知世界,要去探险的感觉,有一种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张感,这也是西方学的一个传统——个人怎么去面对一个未知的,充满各种困难甚至险阻的世界,人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成长,跟环境之间有什么冲突、斗争?
季剑青说,如果对照《旗人风华》书中的内容,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书中呈现的小吴生活并非完全是这样的,作为老北京,他生下来就在一个传统里面,不需要面对未知的世界。小吴从一生下来,所有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从出生,以及生活中一系列的成长阶段,都有一套礼仪,有一套传统文化来支撑,小吴可以在这里面过得很舒服。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我们需要把个体安顿在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已经积累了很多人,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活得很安心,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什么季节该吃什么菜,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世界,传统能够给你提供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支撑。

老北京旧影。
对此,季剑青非常感慨,在当下,因为疫情等关系,我们需要面对一个极度不确定、极度不安全的世界,而这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焦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重新去历险。在这里,北京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担任分享会主持人的高立志进行了补充,在他看来,之所以叫《The Adventures of Wu》,是因为这部著作的背景是庚子事变,庚子事变之后北京沦陷,这也是罗进德一开始不愿意接受《旗人风华》这个书名的原因,因为书中表现了一个大时代,是旗人社会解体的过程。虽然表面上小吴的一生是被安顿得很好的,但事实上这个社会正在解体。
书中的主人公为什么姓吴,而不是赵、张或者李?对此,高立志说,罗进德表示这个“吴”是纪念吴佩孚的。在常人春、常受春的口述中可以看到,常人春一生做北京葬礼文化研究,经历了很多高规格的葬礼,包括宋庆龄、任弼时等,但他感受最深、最豪华、最耐人寻味的葬礼是吴佩孚的葬礼。高立志说,吴佩孚是被日本人杀害的,吴佩孚的葬礼使得北京市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出来祭奠一下自己人。所以书中关于陶然亭,以及钓鱼等的技术,有特别深层的家国感慨。
生命周期:从出生到死亡,从洗三到送三
侯磊自小生长在偏老一套的老北京环境之中,在他看来,《旗人风华》书里的很多细节现在已经流失了,但是老一套的观念、框架还是存在的,这是因人而异和因地域而异的。北京文化、北京民俗到底是怎么回事?从研究角度,如何认识北京民俗?侯磊说,首先要有一个地理空间的认识,要把北京所有地跟过筛子一样筛干净;第二要有时间上的认识,不仅要知道这个地现在是什么样,还要知道这个地历朝历代是什么样;第三,关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生活的人,这块的人都是怎么回事,这块的人都是什么性格,他们都怎么活着;第四,这些老北京人有什么共同的行为。侯磊认为,只有将上述四点都认识清楚,才能往下谈北京的民俗和风俗。

老北京旧影。
侯磊说,他认为,虽然北京有形的城墙没有了,但是无形的城墙还是若隐若现,还是在的。但在这里会有一个矛盾,是应该接着把城墙建起来,维持住?还是彻底不理它?侯磊现场举了一个例子,很多外地朋友问他:“侯磊,你觉得北京小吃真的好吃吗?”他的回答是:“好不好吃不重要,它再不好吃,我也拿它当早点吃了三十多年。”
仔细阅读《旗人风华》,侯磊注意到,从做饭、婚丧嫁娶等很多细节都能发现,书中很多都是满俗,包括饮食风格等,比如书中讲到的涮锅子,一个锅子,先把肉、菜切好摞起来,在锅里一圈一圈放,一摞蘑菇,一摞肉,一摞丸子,粉丝,放好以后添上水,跟锅里面咕嘟咕嘟炖,最早这是火锅,涮的叫涮锅,现在给合二为一,涮的也叫火锅。涮锅就是满俗。因为北京文化受满、蒙等少数民族风俗影响,“北京文化、北京饮食、北京习俗等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
那么,为什么故事发生在礼士胡同?侯磊说:礼士胡同宅门多,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东城区,如果分南北片,以东四为界,东城最阔的地儿,差不多就是灯市口、礼士胡同那一片,那一片宅门最多。

老北京旧影。
侯磊认为,书中的结构非常精密,也很好玩。从孩子长大,最后看着老人去世,这个作品是写人的从生到死,是一个轮回,把出生到死亡,从洗三到送三,整个习俗全都讲了一遍,这个应该叫人生礼俗,把人生礼俗整个过一遍,这是它在结构上非常有意思、好玩的地方。
季剑青认同了这一说法,这一作品原来的书名和现在的书名中都有“生命周期”这个词,生命周期有两个层面,一层是生老病死,从出生到去世,从洗三到送三,包括最后小秃儿结婚生孩子,这就是人生一代一代的往复循环;第二个层面,在这个往复循环过程中,作者把老北京的节令风俗穿插在里面,比如前面讲进香,讲端午,从春天讲冬天,包括中秋节、重阳节放在后面,最后是过年。一方面是讲人的循环,另外一方面是讲时间的循环,节令的循环。季剑青说,这个周期给人一种稳定的感觉,虽然它里面有些地方也谈到好多礼仪、传统在崩坏瓦解,但作者还是想把一种老北京传统生活方式整个表达出来,所以它的完整性是很强的。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罗东
校对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