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截至2018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599.4万例,其中绝大多数缺乏劳动能力,需要长期服药治疗和监护照料。
为此,2017年开始,北京朝阳区试点构建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模式,通过下沉医疗资源、发动社区力量等方式,完善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
精神疾病管理的现状如何?治疗有哪些难点、应该如何改善?就此,新京报记者对话朝阳区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朱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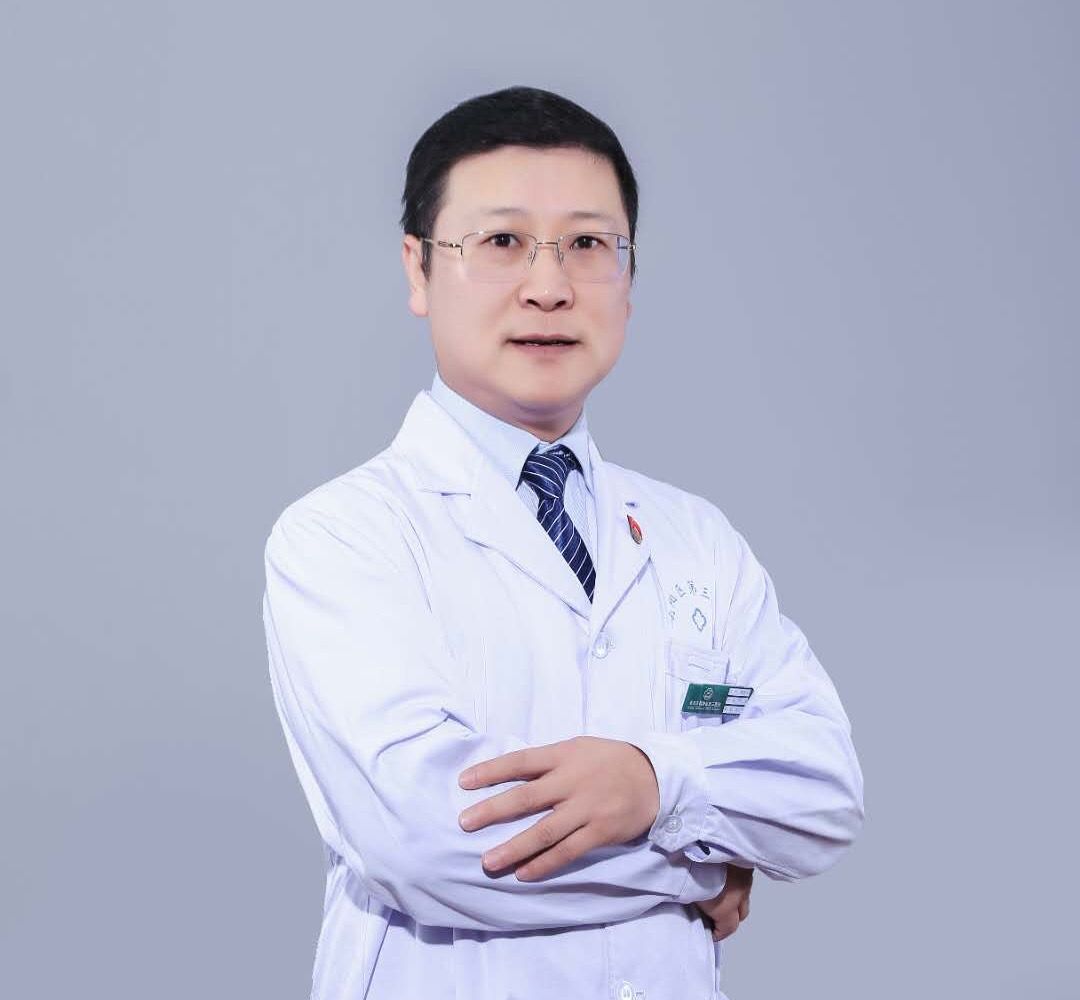 朝阳区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朱庆生。受访者供图
朝阳区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朱庆生。受访者供图
将精神疾病患者集中在机构治疗 不可持续
新京报:你曾经提到,精神分裂症一类的精神疾病,很符合慢病的特性,为什么这么说?
朱庆生:精神疾病有几个特点:慢性、反复、长期、牵延性。临床治疗能让患者临床治愈出院,但并不是痊愈,以后有复发的风险。精神疾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很像,需要长期甚至终生管理。
新京报:现在主要的治疗手段和模式是怎样的?
朱庆生: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患者病情稳定后,主要靠药物治疗。
精神疾病治疗管理方式是存在发展变化的。早期,全世界范围内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是机构化的,把患者集中在一个医疗机构,进行包括康复在内的治疗。后来随着精神疾病种类增加、患病人群增加,发现机构化治疗不是一个可以持续的服务模式,近些年开始去机构化的尝试。
2016年,我去了香港两家精神专科医院之一的葵涌医院,80年代建院时,他们的床位是1400张,2016年实际开放床位减少到800张,30年之间,香港的人口却是一直增长的,这就是去机构化的管理模式,在社区对患者进行管理。
我们现在的工作模式也是这样。患者处于急性期时,在北京安定医院、北医六院等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病情改善后,下沉到区级精神卫生中心进行康复,患者的住院周期就是180天,之后回归社区和家庭,继续疾病管理。
社区、家庭不可缺席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强调社区和家庭的作用?
朱庆生:精神疾病的治疗目标是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康复,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自我救赎”,患者有信心和动力去拯救自己,只有回归到最熟悉的环境,才能更好完成信心再建的过程。
新京报:前面提到,精神疾病有长期性和反复性,怎么确保患者离开医院后,能获得及时的医疗支持?
朱庆生:这就是朝阳区试点构建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模式的初衷。
朝阳区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两个精防医生,对在册的6类重型患者进行日常管理,包括上报、监测治疗、帮助规律用药等。对精神疾病的管理,主要就是服药的管理。但精神疾病的药物在普通药店买不到,必须去精神专科医院开药。为了让患者能就近取药,我们从2017年开始试点在社区建立心身医学科,培养全科医生转岗。
专科医院的医生也会定期下沉到社区,提供一些简易的精神科门诊服务,包括开药,在此之前,社区是不能开这些药的。
新京报:现在管理的难点在哪里?
朱庆生:患者服药依从性、家庭参与度、专业人才数量这三个方面有些欠缺。
精神疾病的特点在于,患者不认为自己有病,也不按时吃药,有的会藏药。今年,我们依托北京安定医院,推广血药浓度检测,对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更准确的判断,此外,长效针剂的使用,也能缓解一些类似的问题,一个月一针,在保证安全性和较好的疗效后,还可以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目前朝阳区已经有数十位患者在免费使用长效针剂进行规范化治疗。
家庭对患者的治疗管理目前是不够的,我们希望下一步通过利用信息化、大数据等手段,让管理医生可以掌握到患者居家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开发游戏等方式,让患者在家里接受一些治疗。
另外,精神专科的医生、护士、辅助人员的数量都是不足的。专业人才资源的配置,有赖于政策导向的推动。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围绕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组织比较少。朝阳区一些社区也在不断完善这一部分,譬如组织患者们结成伙伴、组织社工等提供服务。
未来要更关注老年人及亚健康群体
新京报:未来还有哪些需要着力的地方?
朱庆生:有一些群体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比如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人。
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他们的生活照料、心理陪伴问题如何解决?除了子女的照顾,同时社会的支持也很重要,要让这部分人群有社区可以依赖、有团体可以加入、有活动可以参与,不能独自闷在家里,越闷越不利于疾病的康复。
还有亚健康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争取能让健康人少向亚健康去转化,少让亚健康的人向疾病状态去转化。
新京报:针对亚健康群体的心理服务,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朱庆生:朝阳区常住人口有300多万,我们希望能提供全程的心理健康管理。我们已经开始了核心心理服务能力的建设,这支队伍由三部分组成,核心团队是专科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等专业人士,第二部分是从事于精神科相关工作的外周团队,第三部分是社区团队,比如居委会人员、民警、志愿者等等。这三类人我们已经组织起来了,下一步会通过不断的培训去提升能力。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