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丨后商
受到疫情冲击,失业已经成为全球现象。
从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看,美国5月失业率为13.3%,但媒体指出实际失业率比这个数字要高出3%。在美国43个州中有三个州的失业率都已经超过了20%。此前,高盛预测失业率将达到25%。由于政策限制,高失业率预计在美国将维持两年时间,但由于失业救济金的存在,某些低工薪工作甚至可能会取得高于其就业收入的失业收入。
在英国,劳动力市场上赋闲在家的工人数量似乎处于创纪录水平。在韩国,失业人口达到127.8万人,4.5%的失业率,创下了1999年之后同月最高的纪录。在印度,疫情状态造成了日薪制零工的大量消失,这将令4亿日薪打工者陷入贫困。

2020年3月18日,早高峰时段,一名通勤者戴着口罩穿过伦敦桥进入伦敦城(Tolga Akmen/AFP via Getty Images)。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由于疫情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全球的经济复苏和再就业仍然需要打一个问号。
失业,是一个社会人所面临的诸多危机之一,而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人的危机总是必要的背景。流浪汉小说及其诸多变形,或许是世界文学第一次尝试书写失业及流亡。在最近的三个世纪,经典文本中的失业,总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或社会动荡,比如工业革命、宪章运动、一战二战、经济大萧条、冷战、金融危机等。在当下,作家对失业状态怀有恐慌和忧心。今天,就让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世界文学是如何书写失业的。
十九世纪:
工业革命和自然主义之下人的失业
在英语世界里,现代小说的最早范本可以说是流浪汉小说的变形,摩尔·弗兰德斯和鲁滨逊·克鲁索将失业和流亡延伸到了冒险和寓言的维度,而约瑟夫·安德鲁斯用失业和归乡拯救了自己的爱情。
流浪汉小说所提供的失业想象已经从现代社会中消失了,它所言明的道德败坏、生存苦辛、命运流变在现代小说中锐减了不少,但它几乎是现代生活寓言最近的前身,它的唯一主角(叙事者)、杂凑情节都被后来的文学继承了下来。
从很多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文学,是流浪汉小说的延伸,它们都驯服于“摹仿”。菲尔丁将其小说定义为“散文滑稽史诗”,一举将现实主义文学统一在古老的法则之下。菲尔丁将戏剧改造成小说,用喜剧中惯用的底层有德、底层获胜的叙述来嘲笑人类的罪恶,他的政治情怀也要求他这么做。或许是由于小说刚刚转向现实,他对于农民和工人的书写是很少的,起码相较于狄更斯是这样的。从中文译本来看,《汤姆·琼斯》一书分别有一处出现“农民”和“工人”的字眼。
菲尔丁的喜剧性论断在今天也有它的道理,“生下来不为其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消费大地的果实,这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人类中的大部分必须通过艰苦的工作来生产它们,否则社会将不再履行它承担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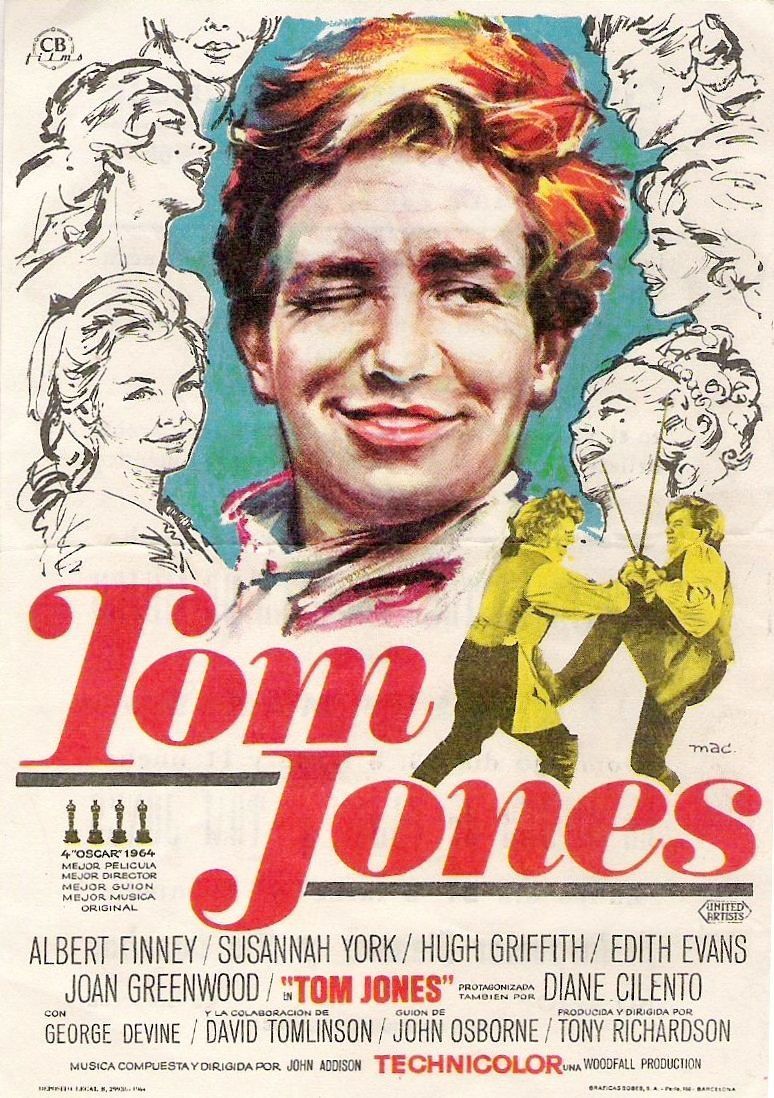
电影《汤姆·琼斯》海报。
工业革命的开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最初的工厂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发展中的学徒制、纪律条文、货币关系和工厂系统逐渐塑造了工人的身份。现代金融和现代工人几乎同时出现了,金融体系和工会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E.P.汤普森指出,“随着时间推移,劳工越来越脱离传统的庄园、教区、社团和家长制政府的控制……”,在劳工和资本,传统和创新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将工人阶级视为被谋杀者,他们的健康和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坏,“到处都可以看到经常的或暂时的贫困,看到因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败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

第一个重大的失业潮爆发于“饥饿的40年代”,劳工运动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第一次劳工运动以破产结束,但在世纪末,劳工革命取得了成功,第二国际也在运动中成立。
工人诗歌(区别于国内刻板定义的工人诗歌)的形成就在宪章运动时期。从这之后,失业作为工人阶级最普遍、最微不足道的苦难,就正式进入了世界诗歌中,它也进入了奥登和威廉斯等典型现代诗人的不完全的工人诗歌中。
宪章运动的领导者欧内斯特·琼斯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在《未来之歌》之中写道,“土地,它为地主霸占,/海洋,它在商人手头,/矿藏充实了债主的钱柜,/还有什么归我所有?/……/军营,教坛,还有法庭,/富贾之子来去自由;/文武技艺都属于他们,/还有什么归我所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远非马克思主义所能概括的。类似的诗歌在世界诗歌中并没有完全消失,它至今还是第三世界的主流诗歌形态之一。
从《圣诞故事集》开始,狄更斯就和贫穷结下了终生的缘分。狄更斯的贫穷是乐天知命的、轻松愉快的,这要归因于他的中产阶级身份。大卫·科波菲尔最早的身份是货行里的小童工(在当时,童工是合法的),在尘污腐臭、老鼠横行中工作,过着困难、饥饿、孑然的生活。后来他就失业(逃)了,在干草堆、啤酒花地里睡觉,但他并没有沾染悲伤,而是朝着他的想象的世界行进着。狄更斯并非社会主义者,他也没有真正在描写无产阶级、城市无产者,他所描写的是聚拢在商业周围的人,或是资产阶级,或是其仆人,在其中,失业景观只是橱窗里的物品。但狄更斯为工作和资本的民主意义做了充分的延伸,他对债务人监狱、贫民院、坏学校大加批判,也抵抗领主、资产者、托拉斯,甚至富人和强权阶层。更为重要的是,狄更斯对幸福生活怀有一种良好的信心,“世界属于那些以坚定的信念、开朗的性情去征服它的人”,这或许是我们对工人阶层和失业群体的一个必要的许诺。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代表作有《雾都孤儿》《远大前程》《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等。(点击可阅读书评周刊狄更斯专题)
出版于1891年的《新寒士街》为我们提供了现代社会最好的(无业的)文人生活写照。乔治·吉辛写了五位生活在伦敦寒士街的潦倒的无业作家。埃德温·里尔登和米尔维恩·贾斯珀是两种典型,前者坚持文学,后者迎合商品社会。里尔登起先赢得了爱情,但转瞬就在贫困中失去了它,如他所说,“爱情是被贫穷吓倒、想法逃走的第一样东西”。凄凉离世时,在病榻上他说,“这个世界不会怜悯一个不能创造或制作某种值钱的东西的人。你可以是个神圣的诗人,可如果没有某个好人可怜你,你将会饿死在路旁。社会如同命运一样盲目和残酷。”乔治·吉辛用他的故事和人生告诉我们:贫困是没有道德可言的。
我们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文学潮流,第一次真正将工人作为主体来书写,它借由左拉先在欧洲后在整个世界流布。左拉的工人和食物、性欲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们也和压迫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工人不得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和遗传的缺陷。绮尔维丝的理想也只是“工作、吃面包、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抚养自己的孩子,不挨打,最好能死在自己的床上……” 值得注意的是,左拉的文学如此之深地构成了文学的第一个科学范式,以至于人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模仿就可以写出一部经典作品,《普通人狄蒂》《嘉莉妹妹》……这些作品继承了左拉对于无产阶级境况的关注。
让我们用托马斯·哈代的《未出生者》结束令我们惊心的十九世纪:“他们匆匆出来,那么忙乱急切/进入他们渴望去的世界,/那无所不在的上帝/驱得他们如一支溃乱之军。”
二十世纪:
战争、后殖民、亚文化之下的职业的失业
在二十世纪,工人的失业状态甚至进入现代主义之中,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殖民地现代文学和西方世界最现代的那批作家中——几乎所有的典型现代主义作家都长期处于失业破产状态。
社会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的预想是对的,劳工运动在二十世纪蓬勃发展,工人争取到了更多的福利。在战争和萧条之后,福利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六十年代前后,失业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它召回了成长小说的传统。随着狂欢的六七十年代走向转型的八九十年代,金融市场开始改变,劳工运动陷入了低潮。与此同时,世界工厂在第一世界国家内外扩张,并在那里创造新的生命、新的暴力。也许,工人从未胜利过,工人也总是无法确保自己有一份工作。
《芭巴拉少校》是萧伯纳对于英国失业救济的揭丑。救世军获取捐款,带给需要救济的失业者们的只有穷困、受冻、挨饿、受罪,“一点面包、糖浆和一杯掺水的牛奶”。老装配工舍里过了岁数无人雇佣,“像匹老马似的送屠宰场”;宪章运动者之子、油漆匠泼赖斯梦想着找到一个活儿,一礼拜挣三十八先令。在序言中,这位改良主义者写道,“贫穷是我们社会最大的罪恶,也是我们社会最可怕的罪行,而我们超越一切的首要责任就是做到不贫穷 。”
在二十世纪中,恐怕没有哪个作家比乔治·奥威尔更关注工人境况了,这要归功于他贫穷的童年、流浪的生活、以及他所选择的正义的写作事业。1928年刊于《公民进步报》的《英国的失业》详细地介绍了一战后的英国失业境况:工业上的统治地位终结了,失业人口有时候多达200万,《失业保险法案》也只是稍微缓和了局面,“救济金”一词充满了对于失业者的污蔑。在伦敦或者曼彻斯特的贫民窟里,穷人们靠劣质面包、浓茶和臭虫维持肉身的存续,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下一届政府会挽救这个残局。基于其流浪生活的《巴黎伦敦落魄记》让失业者轮番上场,其中一个连续五天连面包屑都没吃上,其中一个戏说,“长年流浪的人基本上都是同性恋”。《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更是一次对于底层工人的深入而深度的书写。威根郊区“寸草不生,除了黑烟、石头、冰雪、泥泞、灰烬和臭水外再无其他”……奥威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继续社会主义,以使其更加人性化。

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
当勒内·夏尔在抵抗运动中做出“正确的评断”,“苦涩的未来,苦涩的未来,玫瑰花丛间的群舞……”,斯坦贝克正在大洋彼岸记录着人们对于大萧条的超越,农民被迫迁徙,只不过,他们迎来的是“大灵魂”,是无穷故事中的生命力。在大萧条时代,人们靠豆子和玉米粥打发日子。对于兰斯顿·休斯来说,黑人的日子更苦。他在一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不合作的黑人形象,他会抢任何他想要的东西,“让警察见他妈的鬼去吧”。
像霍尔顿、萨尔或者愤怒的青年一样,奥吉·马奇也是一个现代流浪汉,他从十二岁开始就开始外出谋生,在流动的世界中习得了世故。索尔·贝娄让奥吉摇摆在崇高和现实之间,流浪、走弯路、犯错,让他既个人主义地、又被动地实践一次现代奥德赛。作者试图告诉我们,“每个男人都会成为诗人,每个女人都会成为天使”。这一切都建立在索尔·贝娄对于大萧条的体验之上,那时的他饱受失业之苦。这段经历最早给了《受害者》的主角利文撒尔,他漂泊到纽约,“在东区一个肮脏的、走廊尽头间隔成的狭小空间中,饿得瘦极了”,很久之后他才在流浪者旅馆找到一个职员工作,并成功地从可见的灾难中逃脱了。但人们并不总是这么想。
“我把失业、经济和婚姻上的问题当成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人们总在担心他们的房租、孩子,以及家庭生活上的问题,这才是最本质的东西,是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或上帝才知道具体比例的生活。”能说出这句话的人或许只有雷蒙德·卡佛和亨利·米勒了。卡佛是蓝领之子,一生有很多漂泊和动荡,婚姻里充满恐惧和哀伤,因此,他着迷于琐碎之物、苦恼与肮脏的成长。卡佛没有机会成为凯鲁亚克,和一群嬉皮士搭车、搞革命,像石黑一雄一样。也许村上春树的冈田亨就是从卡佛和凯鲁亚克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世界出发的。
七八十年代的巴西并没有给失业者太多庇护,他们抢劫、强奸,诉诸任何一种暴力。底层人们除了边缘和暴力一无所有,而边缘和暴力本来也是一无所有的:“狗娘养的东西。吃的,喝的,珠宝,钞票,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九牛一毛。在银行里,他们拥有的多得多。他们眼里,我们不过是糖罐里的三只苍蝇。”总之,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
约翰·伯格注意到了移民工人的存在,他们数以百万计、数千万计地存在于欧洲大地。他们的存在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帝国主义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平等和综合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大多数的他们不断经历着偷渡、务工、返乡的故事,几乎是被抛入新殖民主义的系统之中,但他们无疑并不理解这些。他们想要改变未来,他们想的是生存、钱、性,甚至什么都不想,而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得继承祖辈的贫困。他们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马克·吐温笔下那个任意凌辱工人的野蛮世界,而是一个自由而无度的世界。伯格在描述的时候,使用的是不那么抽象的语言,比如这句“金子是从很高的天空掉下来的,所以当它掉到地上的时候,它会陷得很深很深。”伯格让随笔、断片、报告、摄影组合成一部移民工人的档案,这就是《第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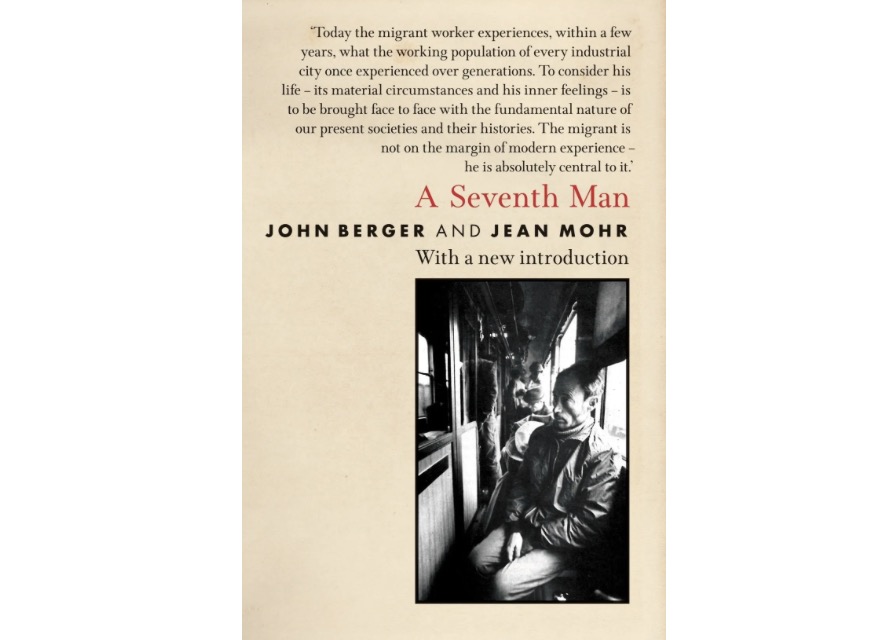
约翰·伯格的移民工人档案《第七人》英文原版(A Seventh Man: Migrant Workers in Europe)。
在非西方世界,失业的书写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处于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交界地带的帕慕克,在他最近的作品中,更多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这或许是因为文学已经令他的阶级下滑了不止一个等级。在他的半自传的爱情故事里,他追随自己的恋人,接触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带着从前他夜巡贫民窟的浪漫情绪和呼愁美学。失业的人们聚集在酒吧,而帕慕克的化身加入其中,和他们喝到了天亮。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只身闯荡伊斯坦布尔的穷小伙麦夫鲁特在世纪末失业了,他无法面对拉伊哈,就漫步目的地在塔尔拉巴什街道闲逛,街道上到处都是小贩推车,他们重新编织了整整一条街。“他的眼睛,因为失业时养成的一个习惯,开始搜寻出售的小贩推车、能和他一起干活的看店的朋友,或是某个可以打折的物件。”再一次,他堕入了帕慕克的忧郁之中,而不是失业带来的困扰和病症,“因为晚上没出去卖钵扎,麦夫鲁特的灵魂萎缩了,也失去了一些激唤他与街道产生心灵感应的东西。”
“几分钟后他将拿着/考勤卡放在打卡机上方/他可以任它掉进去/听它粉碎时的声音/或者他不可以,因为无论是哪种做法这样的日子/都将永无尽头。”菲利普·莱文这首《幸福的每一天》将我们停泊在了二十世纪的末尾。
二十一世纪:
技术时代,生命的失业
石黑一雄在诺贝尔奖席上的演讲中提到,1999年10月,他受邀参观一个集中营,他意识到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在国家间加剧,那个美好的期待已经破产。他表达了对于技术的忧虑,“新的遗传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也可能造成类似种族隔离的野蛮精英教育制度以及大规模失业……”精英们也被撼动了,他们也有可能被塞到失业的货车里。
库切的小说《耻》,象征着白人精英的教授卢里在一场不当的师生性爱关系后没有接受校方的公开悔过的建议,丢了教职,回到开普敦乡村。后来,他的女儿遭遇了性侵,而她放弃了复仇,他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他们醒悟到自己的境遇: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他们一无所有,最后连狗都丢掉了。然而,这只是我们的残酷历史的开始,在后来的耶稣三部曲中,库切给我们的是一个乌托邦“诺维亚”、难民西蒙和来历不明的大卫。库切提供的胜利图景是模糊的,他希望我们可以去做堂吉诃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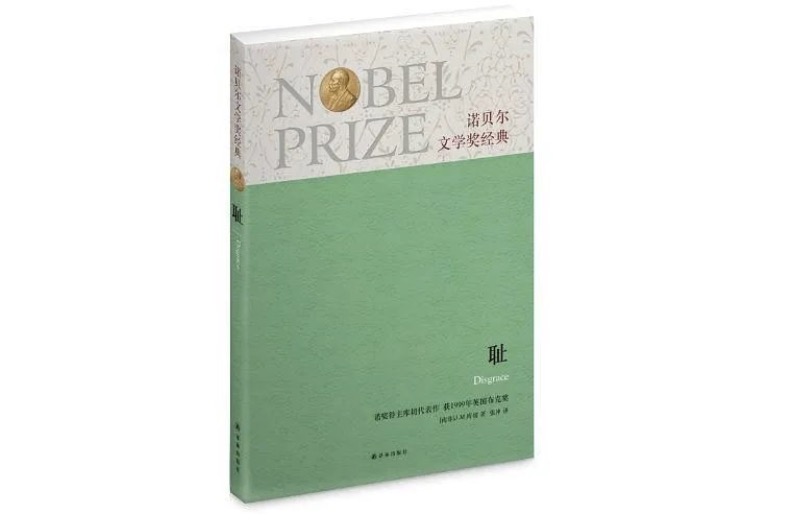
《耻》,J.M.库切 著,张冲 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2月。
在阿兰达蒂·洛伊、迈克尔·翁达杰,或者米歇尔·韦勒贝克、威廉·吉布森等作家的作品中,现代系统在经历了现代主义时期的不完全缺席后重新又回到我们的世界,私密的个人和庞大的世界如此近距离地对话着,小说人物所直接面对的不再是世界的肌理,诸如家具、欲望,而是这个完整的世界,诸如普遍的绝望、无所不在的控制、物质泡沫、心灵的衰迟。每个人似乎都无法在记忆、爱情、事业上找到确切的坐标。失业被放置在诸多的丧失之中,高贵身份的丧失、生活的丧失、记忆的丧失。面对这些,几乎没有人给出确切的解决方案,终点正像弗兰岑所写的那样,是自由而惨淡的。
2008年12月9日,保罗·奥斯特致J.M.库切的信中写道,信贷危机让企业破产,员工失业,“惶恐不安已导致失业问题日渐严重,而失业的人是真的贫困潦倒”。他寄希望于印制大量的钞票以化解这场危机,挽救人们的惶恐。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危害和变化,或许远比2008年的信贷危机所造成的要深刻地多。此后,我们大概会看到世界文学反复书写疫情所造成的经济震动、人生跌宕或悲观保守。
在今日文学世界所提供的超越的现代主义、普世的现代主义方案之外,或许还存在更为有效的方案,而这些是我们在书写的故事。生活在此处的我们,似乎并没有完全分享这些即将入驻经典名人堂的作家们的苦心,我们所经历的或许是他们尚未言明的。我们的工作观念已经不再只是和生存挂钩,它也联系着我们的休闲、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想象。对于掌握了绝对的自由的我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是必须的。我们的工作分散在每一个知识体验里,每一种时间的空隙中,每一块屏幕上,而不再只是“我工作,所以我存在”。而存在在空气中的危机,恐怕也给我们预留一个得体的想象。在新的世界,文学从未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欲望和梦想也不例外。
撰文丨后商
编辑丨董牧孜;校对丨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