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我妈妈其实很妒忌我。”丹麦作家、文学评论家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Leonora Christina Skov)说。我愣了一下,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中国的语境里,“妒忌”一词几乎不会用来形容父母对孩子的感情。
克莉丝汀娜·斯科夫察觉到了我的诧异,她解释道,“这有太多原因了。因为我的成就比她更高;我比她更年轻,比她更漂亮等。我知道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一个母亲竟然会妒忌她的女儿?中国人不会这样说的。但是,对我来说,事实确实就是如此,我要把它大声说出来。我在丹麦做讲座的时候,总有人举手问我,你觉得我的母亲有可能在妒忌我吗?我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能的。”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1976年出生于丹麦的哥本哈根,曾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文学,拥有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目前已出版6部小说、2部儿童文学作品。莱诺拉是美国Ledig House/ Writers Omi,印度Sangam House and Chennai Mathematical Institute,上海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Swatch Art Peace Hotel)等不同国家和地区文艺学术机构的常驻作家。2010年,她获得了丹麦国家艺术基金会三年的资助,以撰写文学作品。她同时是丹麦周报《Weekendavisen》的文学评论员、丹麦艺术委员会三年期的受托人及狂热旅行者。
去年,克莉丝汀娜·斯科夫在丹麦出版了描绘她与她母亲关系的自传体小说《对迷失之物的静谧感受》(The Quiet Sense of Something Lost , Den der lever stille)。迄今为止,这本小说在仅有五百七十多万人口的丹麦畅销了十二万册,引起了现象级的热议,并为她带来了丹麦文学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金桂冠奖”("De Gyldne Laurbær")。
克莉丝汀娜·斯科夫从未想过这本小说会如此受欢迎,她将这归因于她与她母亲的关系具有的某种普遍性。她的母亲在生前十分关注她的生活,对她的期待和关怀也事无巨细。但是,对她而言,这种关注和要求却让她丝毫感受不到爱意和接纳,反而成为了一种负担和压力。在她搬到哥本哈根上大学,准备逃离父母的束缚并寻找迷失的自我时,她爱上了一位女牧师,这使得她与她母亲的关系彻底破裂,也成为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在2019年第四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开幕式上,克莉丝汀娜·斯科夫表示,非常期待中国读者对这本小说的反馈。在采访中,她虽然认为中国与丹麦在文化上极为不同,但她也非常惊讶地发现,在原生家庭里,中国和丹麦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还是存在着诸多的共同点,比如子女感受不到父母的爱,父母过度的爱和要求成为一种负担等。她鼓励大家打破沉默,不要活在父母对自己事无巨细的要求和期待里,说出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也希望能过上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样不管对父母还是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更适宜的状态。
父母过于关怀的爱,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新京报:你在2018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对迷失之物的静谧感受》里面谈到了你与母亲复杂的关系,你能仔细讲讲这本小说与你真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吗?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这不是非虚构作品,我也没有使用真实人名。我从七岁开始写日记。所以,当我在写小说时,需要用到当时的某种感受,我就能从我积累的日记里重新找到我当时的感受。
这本小说与真实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我省去了许多我其他方面的生活,因为这本小说只有400页。在小说里,主要人物只有我、我妈和我奶奶。我要为故事情节服务,就把很多不重要的人物都删掉了。可以这样说,我对我的生活进行了剪辑。但是,我在这本小说里并没有编造什么虚构的情节。因为我已经在我其他的小说里虚构了很多故事,所以在我这本书里我并没有这样做。
新京报:你能谈谈你和你母亲的关系是怎么破裂的吗?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 我的父母不信教,他们是小城镇里的普通中产阶级。我的父亲是军人,我的母亲有着半正式的工作。他们接受不了同性恋。在丹麦,虽然在1989年后,同性婚姻就合法了,但这不意味着大家对同性恋者就没有任何歧视,尤其在一些小城镇里。
我在19岁离开家去哥本哈根学习文学时,跟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女牧师在一起了。与女牧师在一起半年之后,我打算告诉我的父母。我的朋友们都很支持我。我的奶奶虽然信教,但她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然而,最近一次我与我父母同时在家时,我只记得我什么也不敢说,我径直走到我的房间里,拿走了一些旧照片和信件,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还能不能再回到这个家了。我爸爸开车送我回哥本哈根时,我告诉他,我跟一个女牧师在一起了。他没有什么回应,只是说,这很难让你妈妈接受。
结果的确如此。我通过我奶奶得知,我妈当时因此都想自杀了,并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她把我房间里所有东西都烧掉了。所以,我童年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我跟我父母都没有什么联系。
当我27岁时,我妈妈得了乳腺癌。她把这都归咎于我。12年后,她因此去世。我在我妈妈去世后,才写下这本自传体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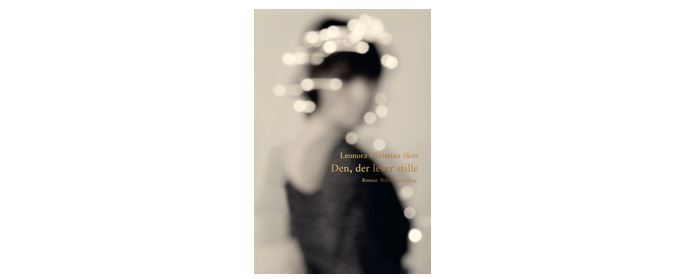 《Den der lever stille》,作者: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出版社:Politikens Forlag,2018年1月
《Den der lever stille》,作者: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出版社:Politikens Forlag,2018年1月
新京报:你爸爸看过这本小说吗?是什么反应呢?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我爸爸读了这本小说,并没有说什么。他只是给我写了一封电邮,告诉我他爱我,并很为我骄傲。对此,我感到十分惊讶,我还以为他也想因此自杀呢,但他依然健在。
新京报:你写这本小说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对你来说,写这本自传体小说是一种反思你生活的方式,抑或是一种摆脱你内疚感的方式?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都没有。我写小说写了15年了。你能从我所有的小说里发现相似的主题:一个不爱她孩子的母亲,或者有着不为人所知的家庭秘密的父母,诸如此类。我对这种写法感到厌倦。我只想写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若我母亲还在世,我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故事,因为我几乎也没有读过类似的故事。许多读者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因此,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你在小说里所描述的母女关系,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吗?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是的。这些经历其实不止性少数群体里会有所共鸣。在这本小说出版之前,我以为这本小说只可能在性少数群体里会有所影响。但是,这本小说在丹麦成为了现象级作品。不管读者的性取向是什么,大家都对书里的母女关系有所共鸣。
我想,共鸣点在这:许多人得刻意表现出父母所期待的样子,才能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和接纳。假如他们的表现不符合父母对他们的期望,他们与他们父母之间就会存在着很深的隔阂。
这个经验是非常普遍的。这本书在丹麦热销了12万册,而丹麦大概只有570万人。男女老少都喜欢这本书,大家并没有把这本书标签为同性恋小说,他们把这本书视为讲家庭关系的小说。对于这点,我也是非常惊讶的。
新京报:几天前你与杨明明导演有一个对谈,她有一部展现中国式母女关系“相爱相杀”的电影《柔情史》。不知道你看过那部电影没有。你觉得在中国和丹麦的母女关系上,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柔情史》电影海报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其实,我也没有期待我这本小说能让中国读者找到共鸣,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文化是如此不同。但是,在那次对谈中,我也非常惊讶地发现,许多中国人在母女关系上也有着与丹麦人类似的问题。当时,许多听众举手站起来,分享了许多自己感受不到父母对自己的爱意的经历。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跟母亲关系破裂,有的人抱怨自己的母亲过于关心自己的生活了,而他们想要过自己的生活。这就跟我的经历很相似。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妈妈就非常关心和在乎我的一举一动。因此,当我听到这些类似的感受时,我真的很感动。当然,在中国,你们从父母的“爱”中获得自由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在丹麦,我们则能更容易地摆脱父母的束缚获得自由,这也是整个丹麦社会对每个人的期望。
这种爱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我觉得如果父母要孩子的话,就不应该对孩子有着非常明确的期待,比如希望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父母应该要让孩子自由成长,在这个世界上,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成为他们自己。
我的父母就对我有着许多十分具体的期待。比如我父母希望我结婚生子,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在他们眼里当作家并不是什么正经工作。他们觉得我不可能靠写作生活,希望我能有“正常”的工作,但我对那种工作不感兴趣。
我其实不认可“每一个母亲都爱着他们的孩子”这样的话,我不觉得这是普世的。因为我还发现,我妈妈其实很妒忌我。
新京报:为什么?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这有太多原因了。因为我的成就比她更高;我比她更年轻,比她更漂亮等。我知道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一个母亲竟然会妒忌她的女儿?中国人不会这样说的。
但是,对我来说,事实确实就是如此,我要把它大声说出来。我在丹麦做讲座的时候,总有人举手问我,你觉得我的母亲有可能在妒忌我吗?我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能的。
“在西方,女性的愤怒是一种禁忌,而我要打破这种禁忌”
新京报:说实话我有些惊讶,丹麦是世界上女性权益和性少数群体权益保护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你的经历中,你母亲是非常难以容忍同性恋的。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因为我之前写过几本小说,我要做讲座宣传。我见过许多读者,每一次讲座里,总会有四到五人,在出柜上跟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尤其在小城镇里。在丹麦,还是有相当多的人信教的。
当然,总的来说,现状是越来越好了,丹麦政府禁止歧视性少数群体。我觉得性别上的平等和性取向上的平等,已经成为了丹麦的核心价值观了。但这也不代表丹麦社会对这些不存在任何歧视。
新京报:所以,在公共空间里,明目张胆的歧视不见了,但是这种困扰变得更加个人化了?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是的。在很多情况下,这都是比较私人的问题。
新京报:在中国,许多性少数群体并不会向父母出柜,他们也许会形婚。你怎么看待形婚?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当我出柜时,我当时的女友并没有对她父母出柜。她跟别人介绍我,说我只是她的朋友。我觉得这像谎言。这也是我跟她分手的原因之一。我不能在这种谎言下生活。我必须得出柜,因为这样总会被发现的。形婚在以前的丹麦也是比较常见的,其实这也总会被发现的。
新京报:你对那些要对父母出柜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我知道这里的情况与丹麦大为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意味着很多东西。所以我很难给出什么建议。我因出柜失去了许多东西。所以要出柜的话,你必须要坚强地生存下来。
我觉得在那段最困难的时光里,愤怒是支撑我的力量。我当时非常愤怒。你也知道的,在我们的文化里,女性是不该如此愤怒的。假如我没那么愤怒的话,我就不会没有今天的生活。我当时很生气,因为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要改变它。所以我变成了女性主义者。这也是丹麦人首先知道我的身份。因为我首先是一个公共议题辩论者。这帮助了我,因为,这样我能说出我的心声,它给我力量。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
新京报:是愤怒让你变成女性主义者?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不,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父母不接受我。我需要女性主义,因为我需要某种理论的指导,帮助我分析为什么这种歧视会存在。这种父权制下的体验,使得我们需要女性主义来去理解这个社会。这是我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原因。
我愤怒只是为了活下去。我不是说我是一个愤怒的女性主义者,愤怒只是我做任何事情背后的驱动力。我要生存下来,我就必须愤怒。
新京报:这种愤怒是私人化的吗?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是,我想每一个作家都是愤怒的。虽然作家不会一直愤怒,但是在写书的某些时刻,你是需要一种力量去继续你的写作的。我也是这样,虽然我并不是一直愤怒,但是在我写书的某些时刻,我需要愤怒来继续创作,写出凌厉的作品。在西方,女性的愤怒是一种禁忌,而我要打破这种禁忌。
新京报:“女性主义者”这个标签会困扰你吗?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曾经会,现在不会。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标签在丹麦是很难被严肃对待的。因为人们总觉得我在写女性主义小说,进入不了主流视野。我这本小说是我第一本被广泛阅读和接受的小说。在这之前,人们也许觉得我是一个愤怒的女性主义者,痛恨男人。
我当然想被广泛接受了。于是,七年前,我就不参与公共辩论了。我沉默了。我专心写我的小说。现在这个标签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丹麦人对女性主义的看法改观了很多。做一个女性主义者不再是某种“污点”。
现在在丹麦,许多人都在出柜。这不一定指性取向,还指他们自己的本心。他们向父母朋友出柜,表明自己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这也是这本小说受欢迎的原因,因为它鼓励人们站出来。
“让不想当母亲的人当母亲,这是非常糟糕的主意”
新京报:#Metoo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有人认为这让沉默的女性有机会发声,也有人批评道,#Metoo运动让这个社会更加的禁欲,大家在性观念上会更加保守。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我觉得发声本身就很重要。我们得对侵犯我们的东西说不。有人之所以不喜欢#Metoo运动,是因为他们拥有这个特权太久了。不管如何,对所有人来说,更舒服、合适的氛围肯定是更好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美国亚拉巴马州最近通过的最严格的堕胎法案?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你觉得呢?我觉得男人不可以决定女人要不要孩子。我妈妈就不想要孩子,是我爸想要孩子的。当然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例子。总之,让不想当母亲的人当母亲,这是非常糟糕的主意。
新京报:面对着几年来全球右翼的崛起,你对未来女性主义是什么态度?
莱诺拉·克莉丝汀娜·斯科夫:我一直都很乐观。不然,当女性主义者也太悲惨了。现在美国在退步。不过,保守力量永远都在那里。我们也有#Metoo运动推动进步。抗争是不会停止的。
总体来说,在丹麦,女性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比以前是更加容易的。比如说,我没有孩子,也不想要孩子。我以前经常会被别人问,为什么不要孩子?是你不想带孩子吗?我当时只能找借口:我没有时间、我要写书、我一直在到处旅游、我对孩子没兴趣。而现在,我再也不会被问到这些问题了。我相信未来还会更好。
作者:徐悦东
编辑:徐悦东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