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话许纪霖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另一种理想主义》《家国天下》等
1.1
社会力量在五四运动中崛起
新京报:五四运动是一场为捍卫国家主权而发起的爱国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由学生发起并主导,它在理念上有怎样的特点?
许纪霖: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从思想史角度而言,清末民初和“五四”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前者是一个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狂飙的时代,因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国已经建立,知识分子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签订“二十一条”。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持国家有机体论,认为国家和国民是一回事,但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法变了,他们觉得国家不一定代表国民,国家只是工具。国家观念变化以后,他们就开始注意到清末民初不特别强调的文明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核心话题就是文明。
五四运动表面上争的是国家权益,但其实五四运动的宣言讲得清清楚楚,争的既有国家权益,也有世界公理,他们把文明也看作是一种公理。之所以要反对巴黎和会,不仅因为它侵犯了中国的利益,还因为它违背世界公理。由此可见,“五四”知识分子爱国胸怀之博大。当时,无论是老一辈的陈独秀,还是年轻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都懂得用一套世界性的文明语言来伸张国家权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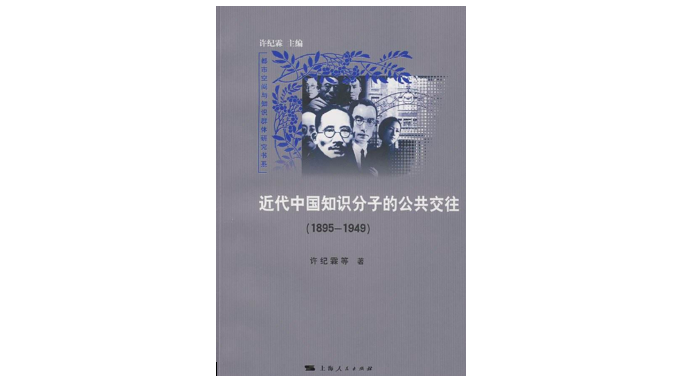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作者:许纪霖,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
新京报:1920年,傅斯年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中国算有了‘社会’”,“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五四运动中,学生、工人、市民群体自觉地结成联盟,并通过游行和罢工影响国家决策,社会力量的崛起,算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功绩吗?
许纪霖:可以这么说。实际上很有趣,很少有一个运动在它刚刚发生的时候就被命名,五四运动恰恰是一个例外,它在当月就被命名为“五四运动”,这就涉及五四运动如何来自我理解的问题,当初的理解和今天是有差异的。当时,无论是傅斯年、罗家伦这两位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和宣言起草者,还是陈独秀、胡适,都更多地把“五四”理解为一场社会运动、公民运动,一场国民的觉悟。这是因为此前的政治运动,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召开国会,都是在政治层面来解决政治问题,没有人想到要去发动社会运动。过去都认为社会是消极的,即便像辛亥革命这样的改朝换代,社会也是不动的。
“五四”一开始是学生运动,但是单纯的学生运动并没有成功,最后奠定胜局的是6月初上海发生了罢工、罢课、罢市运动。“三罢”的参与主体,从学生变为广义的城市市民阶层,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商人、工人和一般市民。清末并不缺单纯的学生运动,公车上书已经有过,但是只有五四运动生长出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世界媒体的强烈关注,但等到上海发生“三罢”以后,就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这个压力北洋政府受不了,所以马上就妥协了。

美国摄影家詹布鲁恩拍摄的五四运动示威者,他们手持“卖国奴曹汝霖”、“还我青岛”、“青岛是中国的”等标语走上街头。
1.2
百家争鸣的“五四”时代
新京报:五四时期之所以有各种思潮蓬勃涌现,与当时在知识积累、传播手段、文化体制、国际环境等有哪些关系?
许纪霖:首先得益于公共传媒的兴起,公共传媒在晚清已经开始出现,戊戌维新运动之所以能够这么磅礴,和当时出现了报纸有关。到民国以后,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更丰富了。其次,是欧战的爆发,虽然中国只派出了劳工,但是中国人对欧战的进展非常关心,人们把欧战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包括《新青年》早期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要走什么路?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德国式的富国强兵路,一种是英法式的以文明为主流的一条路。一开始,包括《新青年》在内的很多舆论都认为中国应该学德国,因为在欧战早期德国所向披靡,但是后来随着战争的持久,德国就撑不住了,然后中国知识分子就越来越明确要以法为师。
可见,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已自觉地把自身的民族命运和人类文明的大命运联系在一起。当时杜亚泉办的《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非常详细的欧洲报道,而且不仅是关心军事上的战争,还包括思潮上的战争,将各种新思潮及时介绍进来。到“五四”后,已有了一批懂英语、法语的海归,不必再借道日语,已可以直接对新思潮有所了解。欧战把中国和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作者: 许纪霖,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
新京报:从国内局势来看,民国初年的混乱格局是不是也给思想文化的发展传播提供了空间?
许纪霖:北洋时期可以说是政治上很黑暗的时代,却是思想上的黄金时代。中国历史上有一条规律,思想最活跃的时候都在乱世,比如说春秋战国、魏晋时代、明代末期。但凡太平盛世,王权实现大一统,通常就只能做修《四库全书》之类的文献整理工作,思想上并没有什么创造力,更难说有什么文化上的突破。五四运动,学生最后之所以能获胜,与北洋政府内部的政治势力矛盾也有关系,直系和皖系之间存在斗争。
2
对话杨念群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著有《五四的另一面》《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等
2.1
以国际视野看“五四”
新京报:四月初,你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参加“五四运动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嘉宾对五四话题有什么新视角,或提出了什么新的学术话题?
杨念群:提供了一些如何从不同国家观察“五四”的视角,在学术上也开拓了一些视野。比如说,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官话变化,或者普通话是如何成为正统话语的,再比如国语运动跟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另外,比如一些学者发现“五四”同期埃及也掀起了类似的改革运动,这就提供了一个从中东地区来观察五四运动的机会,可以把“五四”与当时中东发生的事情进行彼此对照。还有,比如从日本、印度的角度,怎么来看待五四运动。
除此之外,在这次的学术研讨会上,还有一些我们平日可能不太注意的视角,比如谈论胡适的女性主义,或者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也算是有点新鲜感。总之,把五四运动放在国际视野来谈,不同国家和文化语境中的学者一起各自从不同立场来进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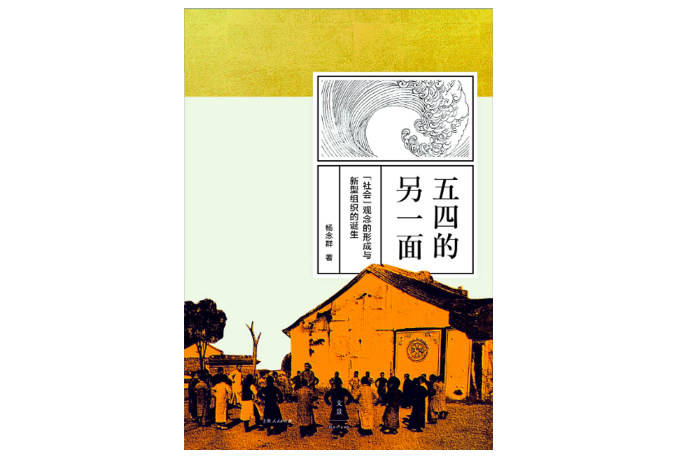
《五四的另一面》,作者: 杨念群,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纪文景,2019年4月
新京报:你的《五四的另一面》并没有去不断分析和挪用史料,而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写作范式,更多的是从理论方面去解释“五四”,似乎杂糅了历史分析、史学理论、观念变迁、思潮变化等的综合写作方法,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写作范式?
杨念群:我并不特别想用什么历史理论来阐释“五四”,毕竟历史理论处理历史事件太过于模糊化,我是想把当时的社会现象揉到一个贯通的视野里;也就是看“五四”这面多棱镜,我们不能仅仅单纯看它的一面,每一面都应该关照。我对过去的“五四”研究特别不满的地方,就在于动辄就只谈民主与科学。它们难道不是从晚清到民国一直都在的话题吗?
由于民初政局的混乱,让大家不再相信上层设计,所以大家开始往社会层面走了。科学主义当然也是“五四”的主题,但绝对的科学主义在五四时期有谁在谈?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在谈,但它不是“五四”的主调。在我看来,社会和文化才是“五四”主调,比如文化里涉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社会层面包含社会主义、团体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再比如,道德伦理的“莫拉尔小姐”,当然它也是社会层面的。

五四运动中,参与游行的北京财政商业学校学生。
2.2
当时参与“五四”议题的是哪些人?
新京报: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当时请出了“莫拉尔小姐”,提出了道德伦理层面的议题,却是以反伦理的面貌出现的。
杨念群:对。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以反伦理的面貌出现之后,找不到替代之物。所以,这里面有两条线可以走,一条线就是鲁迅提出的“娜拉出走之后”,摆脱家庭束缚之后,你往哪儿走?没有比较好的生存方式,也没有比较好的职业道路,那时候的女性基本就是类似于做女招待,连担任女教师的都很少。
这里的反伦理,实际上也是重建伦理的过程,但较之于反伦理则显得更加艰难。尽管“五四”前后提出了诸如个人主义等争议性话题,但个体必须重新寻找到新的社会网络,无政府主义最后不就玩不下去了吗?再比如当时还有人提出回到保甲乡约等,也就是类似于回到一个相互制衡的区域空间中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新京报:所以,在谈论“五四”的时候,又不得不回到科举制废除后的历史脉络中去?
杨念群:对。实际上,五四运动很大程度也是后科举时代的产物。新文化的第一拨参与者是蔡元培、梁启超等老科举人,他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只是科举废除之后变得特别激烈,它们是反体制的精英。中间那批人就是大学精英。再后来,就是类似于胡适等海归青年。
这些群体考虑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早期诸如梁启超他们对上层政治反感,所以他们有着一种反体制的冲动。大学里的精英往往有时候就显得像文青,类似于朱谦之等人谈抽象的文化。海归们谈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当然,他们也有开始向基层走的倾向,比如到下面去看工人农民。后来,李大钊等人基本就依靠组织活动了。所以,我认为,在谈论“五四”的时候需要注意到核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框架。
3
对话欧阳哲生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等
3.1
“五四”在新文化运动的延长线上
新京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常被放在一起考察,五四运动的政治化转向之后,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分裂。关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新文化运动人士为何会产生分歧?
欧阳哲生: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打断了原有的新文化运动进程,他原本设想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是一场非政治的文化革新。但实际上,对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在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早就有不同看法,比如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就把文化和政治紧密关联在一起,他们在从事新文化运动事业的时候就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所以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们顺应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趋势,把文化运动逐渐推向政治,最后投入创建政党的事业。
其实,胡适的看法在当时并不是主流,大部分人还是对政治有关怀的,因为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很多人都跟辛亥革命有密切关系,是原来的革命党人。
比如,陈独秀原来是同盟会的,参加过辛亥革命;蔡元培更是同盟会元老,是搞过暗杀的革命党人;李大钊的政治归属相对多元,他不属于同盟会,而是在日本学过政法,跟梁启超等一批搞立宪的人有过联系。此外,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本身就具有反袁世凯的倾向,背景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所以,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有政治关怀,只是为了不在政治上锋芒太露,所以才虚晃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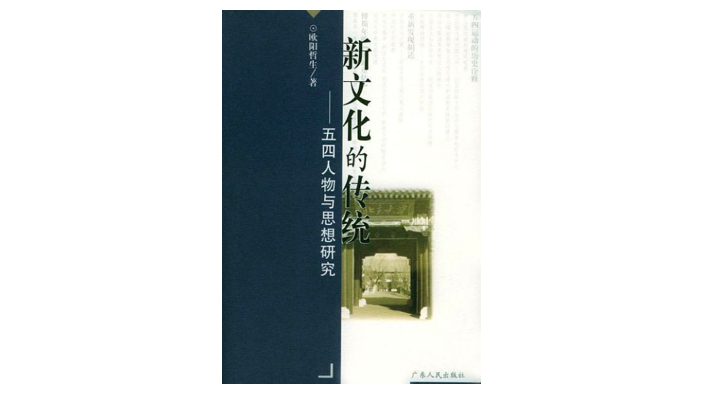
《新文化的传统 : 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作者:欧阳哲生,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新京报:如果没有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新文化运动按照其原有的发展路径,会转向激进的政治行动吗?
欧阳哲生:在民国初年,政治的激进化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政治情形太坏,所以必然引起反弹。反弹是两种势力的对决日趋激烈,从而导致政治激进主义越来越强化,激进主义不完全是一种自我的选择,它和对手有一定的关联。因为敌人太残酷,所以只能用更加暴力化的手段去反抗。从袁世凯开始,当时的统治阶级北洋军阀就是比较残酷的。
新京报:蔡元培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但五四运动以后,越来越多的文学青年、学术青年变成了革命青年,导致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知识结构上的,还是外部形势的裹挟?
欧阳哲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政治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一条主线,“五四”以后,政治的地位更趋显著。政治的核心是革命,所以学生从课堂走向游行队伍,最后走向战场,弃学从戎,这种情形在当时非常普遍。

1919年6月,拘捕演讲学生的军警。
3.2
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赛跑
新京报:你在《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中提出,“五四”有两大传统,即激进主义的革命传统和渐进改良的传统,这两大传统在思想上的主要分野是什么?
欧阳哲生:主要是在改造社会的途径上,自由派主张温和渐进,认为用暴力的方式推翻一种制度成本太大,对社会的伤害太大;而革命派为了快速解决社会问题,不排除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一个政权。在五四运动中,两种派别姻缘结合,为运动的推进注入了双重动力,但两大思潮毕竟渊源各自,取向不同,个性迥异,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分化离散的结局。
五四运动发展并强化了两种观念:革命与民主。在观念形态上,革命将人们引向对旧制度、旧思想、旧习俗、旧生活方式的反叛;民主则成为人们谋求建立新社会、新政治、新道德、新生活方式的价值标准和观念基础。两者并非一回事。革命不等于民主,相反,革命过程中时常伴随不容忍,伴随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有时会与民主冲突,甚至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民主也并非革命,民主是各种政治派别都要遵循的行为规范,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相互依存的社会契约,是承认人各有其价值并听其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民主是一个历史过程,谋求民主的方式,渐进往往比革命更合理、更富有成效。

《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作者:欧阳哲生,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新京报: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为何激进主义会占上风,渐进主义则被边缘化?
欧阳哲生:这里面的原因非常之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人都对解放、对现代化、对社会改造有一种急迫心理,这种心理会对迟缓的温和的渐进式的手段不耐烦,最后都选择比较快的那一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5年孙中山和严复在伦敦的一次会谈,严复是主张渐进的自由派,而孙中山是主张革命的。孙中山问严复,改造中国的途径从哪里入手?严复说,只有从教育入手,一步一步地改。孙中山就感叹了一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意思就是说,要等到黄河变清澈,要等到什么时候,那时候人都可能不在了。他觉得通过教育的办法来改革太慢了,因而急切地要求革命,所以革命始终在重大的选择关头都处于上风。
新京报:你致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数十年,出过许多著作和文章,这个历史时段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作为百年后的读者,阅读和了解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何在?
欧阳哲生:在我看来,“五四”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笔思想遗产,从思想的丰富性而言,没有任何其他时期可以与之媲美。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中,“五四”是中国思想最开放、文化发展最迅速、社会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但凡是这样的历史阶段,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思想灵感和营养也是最多的,可供探讨、研究的话题也是最多的。在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五四”是各种现代性价值观念在中国生根的关键点,例如民主、科学、自由等观念传播到中国来,它集聚了多种文化能量和思想矿藏。
“五四”成为纪念日,从1920年的第一周年即已开始,此后每年都会出现纪念性的活动,所谓纪念其实就是重新解释,不断地翻新,让现实与过去对话,具有再造历史的作用。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是以追加的形式赋予的,我们也通过不断阅读和对话,挖掘出它的更多思想价值。
作者:徐学勤 萧轶
编辑:徐悦东 校对: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