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今天讨论‘996’,实际上欧洲已经讨论过了。中国社会现在是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在此之前大家就是拼命赚钱,不太关注这些问题,解决吃饱问题之后,才讨论值不值得这样做。”雷颐在讲到我们对19世纪欧洲历史的认识时说道,“其实,社会福利制度就是俾斯麦建立起来的。”
对于欧洲来说,19世纪是一个进步的世纪,也是一个灾难的世纪。对于中国等东方世界来说,又是受到冲击和学习的世纪。在面临欧洲文明的冲击时,中国和日本为何会有着不同的反应?各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它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对于现代的中国来说,回看十九世纪的历史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4月14日,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工作室联合缘法思享汇、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研究生会,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燕京学堂报告厅举办了系列图书“企鹅欧洲史”的读书分享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彭小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研究所雷颐与读者探讨了这些问题。历史已离我们远去,但它对于我们理解当下,进而慎重地把握未来不可或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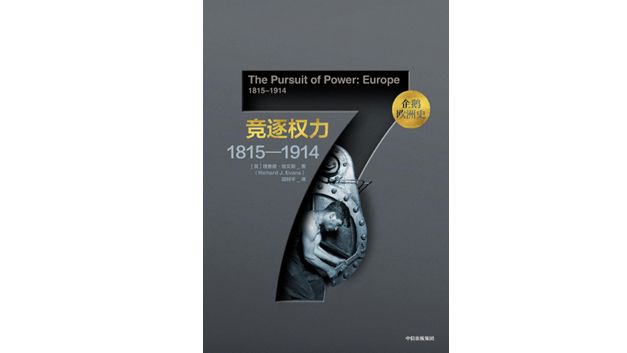
《企鹅欧洲史:竞逐权力》,[英]理查德·埃文斯著,胡利平译,新思文化丨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12月版
十九世纪是进步的世纪
也是灾难的世纪
彭小瑜分享了他阅读《企鹅欧洲史:竞逐权力》的心得。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埃文斯认为,争夺权力和霸权是理解19世纪的欧洲历史的关键。他还认为,权力欲造成了19世纪的很多灾难。因此,19世纪既是进步的世纪,也是灾难的世纪。
我们通常在描述法国大革命时,色调会比较阳光正面。但是,理查德·埃文斯强调了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的欧洲战争的破坏性。拿破仑入侵俄罗斯就有40万人战死。法国革命后的欧洲战争一共导致了500万人死亡。如果考虑战争伤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这其实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还严重。

《1808年5月3日枪杀马德里抵抗者》,作者:(西班牙)弗朗西斯科·戈雅,描绘了法国军队镇压西班牙抵抗者的画面。
在1812年,俄罗斯人为了抗击法国军队,实行了焦土政策,在莫斯科的9000栋房屋中7000栋被焚毁,8000多个店铺和仓库被烧,98%居民逃离莫斯科。基本上整个莫斯科都被烧掉了。而重建莫斯科则花费了数十年时间。
在伦敦水晶宫里举行的第一届世博会,展示了工业革命成果和社会进步。但是,与这次展览大致同一时期,欧洲各地出现了马铃薯枯萎病以及它导致的饥荒。在有着大约五百万人口的爱尔兰,有一百万人死于饥荒,而另外一百万人移民到海外。这次饥荒对欧洲社会的冲击力非常大。而在那个闹饥荒的岁月里,爱尔兰同时还在出口食品。理查德·埃文斯指出,如果这些被出口的食品用于救济灾民,是可以让爱尔兰避免这次毁灭性的灾难的。
19世纪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的时期,同时它又是进步的时代。俄罗斯重大的社会改革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发生的。俄罗斯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但是,农奴制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俄罗斯的社会问题,所以后来发生了十月革命。农奴制改革及其结果并没有在制度上和文化上让俄罗斯追赶上欧洲更加先进的国家。
19世纪是工业革命的世纪,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非常严重。比如老式火柴要使用白磷,这会导致火柴女工白磷中毒,她们的面部骨头会坏死、腐烂化脓。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会不择手段,有些在理查德·埃文斯这本书里讲到的故事,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理查德·埃文斯在书中还提道,英国中产阶级的学生在1840年平均比贫民学校的学生高出23厘米,中产阶级的婴儿成活率在1900年是96%,而同时在伦敦贫民窟只有33%。在工业革命时期以及此后一个阶段,工人阶级的状况很悲惨,德国19世纪末的“工人阶级往往只买得起没人要的东西,破了的鸡蛋、发霉的面包、磕碰过的水果、动物内脏,还有未售出的不新鲜肉类和鱼”,平时只能吃面包、马铃薯和玉米糊。
俾斯麦最早在德国开始试验国家福利政策,试图以此应对来自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在一战前夕,德国疾病保险和工伤保险分别覆盖了1500万人和2800万人。瑞典在1913年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全面医保制度。1910年法国实行工人退休金制度。英国在一战前后有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包括退休金制度、工人住房补助、疾病保险和失业救济,冲击了以不救济“懒人”为原则的《济贫法》。但是,彭小瑜提出,英国的教育平等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大量工人子弟无法接受良好教育,贵族学校盛行。直到现在,我们还看到世界各地的权贵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这不是一个好的传统。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理查德·埃文斯提到,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让·饶勒斯在一战前夕因其反战立场被刺杀。而且,凶手还被宣判无罪,因为“陪审团成员坚信,战争是必要的”。在德国,最早支持战争的“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所以“在所有支持战争的集会上,如潮人群中几乎看不见一顶布帽子,看不到一个穿工装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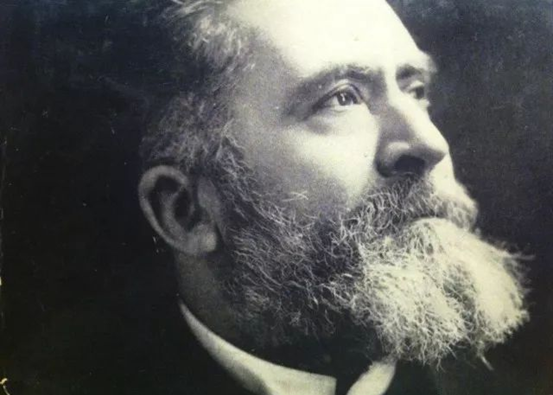
让·饶勒斯
彭小瑜认为,在理查德·埃文斯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所遭遇的多次灾难,都是因为各国和各派别之间的争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地位的争夺。这是19世纪历史让人感到遗憾和悲伤的方面。社会福利制度的实施让西方内部的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但是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存在着让人失望的种种问题。欧美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东方国家是不利的,也逼迫东方国家去面对现代化的挑战。
在面对欧洲文明的挑战时
中国和日本为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雷颐则从东方的角度来看19世纪欧洲对东方的影响。雷颐认为,19世纪是中国认识西方的一个转折点。在19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界轴心文明国家,其他国家是中国的藩属国,有着天朝上国的心态。其实,19世纪的中国有机会看到西方的发展和进步,但是我们都一概无视了。早在明代,就有传教士来到中国,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最后也并没得到什么发展。
在清代,由于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清政府只在广州一个地方开放了口岸通商。所以,其实在这几百年来,广州可以是接触到外面的世界的,问题就在于,这一切都没有引起重视。在19世纪欧洲已经有了蒸汽机轮船,也来到了广州,但并没有引起当时中国人的重视。商船里的先进武器,清政府的海关也不以为然。等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才发现,我们对敌人一点都不了解,才叫人去澳门了解。
雷颐表示,其实在英国的大船来广州之后,有广州商人就开始仿造了,但是造完了之后就被当局拆掉,因为当时的清朝的产权制度也不完整。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学习技术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难事。但是,朝廷允许大家学很难。第一次鸦片战争14年之后,清朝才用上洋人的武器,这还是曾国藩自己的军队先用起来的,因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效果很好,朝廷才允许使用。当时洋务派还要求造武器,这花了22年,清政府才允许生产洋人的军舰、枪炮。而日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使用洋人的武器了。
这可见当时欧洲对东方的挑战,在中国和日本引起了不同的反应。鸦片战争的经验反而成为了日本的知识。《海国图志》在出版之后就被封禁了,但这本书传到了日本,并在几年之内翻译了二十多个版本。这本书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非常大的启蒙作用。
雷颐谈道,当时有一个日本人叫高杉晋作,被派往清朝考察,他来到后很失望,发现清政府不允许造洋枪洋炮,他非常推崇的《海国图志》,也被禁了。他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他回日本后写了几篇文章,说本来他觉得日本要学清朝,但是清朝不准造洋枪洋炮,连启蒙日本志士的《海国图志》都禁了,所以日本不能学习清朝,得脱亚入欧。整个日本的知识界或武士界都觉得中国不行,必须脱离中国的影响。这就是欧洲的冲击对中日两国的不同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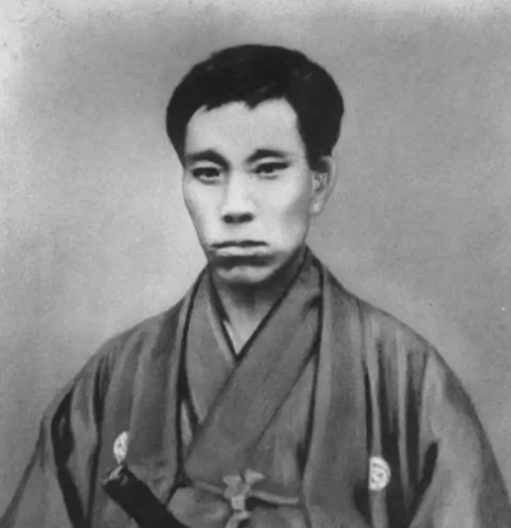
高杉晋作
彭小瑜表示赞同,“我们一开始很迟钝,不过受到侵略后,很快就转过这个弯来,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彭小瑜还提道,利玛窦当时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其实也带来了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思想和其他文化观念。凯恩斯曾说过,他的经济学灵感有一部分来自中世纪的欧洲,因此认识到消费、流通和国家干预对经济活动的重大影响。很多历史学家也意识到,中世纪欧洲就有这种经济思想的萌芽。
彭小瑜举例道,在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里,夏洛克就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另一个商人安东尼就被描写为有着基督教道德的好商人,反对高利贷。中世纪教会批评高利贷的目的不是反对市场经济,而是强调私有财产和经济活动的社会公益性。“当时的教会人士,譬如方济各会的修士,注意到教会为了慈善目的进行的经营、从事的金融和工商业活动,譬如向穷人发放的救济和无息贷款,会刺激消费,加强经济的活力,而教会对高利贷和为自私目的囤积财富的批评,不仅反对贪婪,同时也是在反对让财富退出社会流通,是对经济活动方式的一种干预。”

彭小瑜
而这种先进的思想,是利玛窦试图传播给当时的中国人的观念之一,只可惜在当时不可能被人理解和重视。彭小瑜认为,像徐光启那样有着高深文化的教徒,是否能够比较全面读懂这些传教士内心深处的东西,是否能系统地读懂他们试图传播的西方文化,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重要题目。
彭小瑜:蔡元培的基础教育思路也许有缺陷
理查德·埃文斯在书里也谈到了欧洲国家之间的文化和制度差别。英国的教育制度就非常有问题,“我们一般人往往不知道英国在近代历史上有严重的教育不平等,而且这一现象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尖锐的批评。”免费和普及的国民教育,作为一种理念和制度,在英国近代成长得很艰难。
“如果你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你很有天分,可以上免费的国立学校,但是需要通过严格的入学资格考试,否则你初中一毕业就去打工了。普及高中曾经是一个被争论的问题,因为资产阶级认为工人不需要接受太高的教育。国民教育应该必须是全国统一标准和质量的基础教育。英美两国的国民教育在原则上被看作是地方社区和政府的事情,一直有比较严重的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昂贵和精英色彩浓厚的私立学校在英美一直比较重要。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选择学习英美的基础教育模式,强调地方政府的主导。这一范式对我们基础教育长期不均衡的状况应该有很大影响。大家也都知道,在美国很多地方有经济和社会秩序比较差的社区,那里的公立学校就会很差,而附近中产阶级的社区会有很好的中小学。这种地域性教育不平等对健康的社会发展和阶层流动妨害很大。”
彭小瑜认为,蔡元培设计的基础教育政策应该是有缺陷的。“法国大革命以后,共和派提出的教育方针是全国统一的,也预期在全国有统一的实施,提出了国民教育的概念。我们在民国时期固然不具备实施均衡统一国民教育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为各省各地的情况很不一样。这可能是蔡之所以选择英美模式的原因,允许基础教育有比较大的地方差异性,减少中央政府的负担。这个问题需要专家去系统研究。但我们对民国教育的弊端和问题需要重视。蔡先生与江浙财团关系密切,他是否为了保护江浙地方利益,放弃了法国那种强调全国基础教育标准统一的体制?像现在日本、韩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他们强调基础教育严格整齐的统一标准。所以我们延续自民国、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是否跟蔡先生这个顶层设计有关联呢?”
作者: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吕婉婷;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