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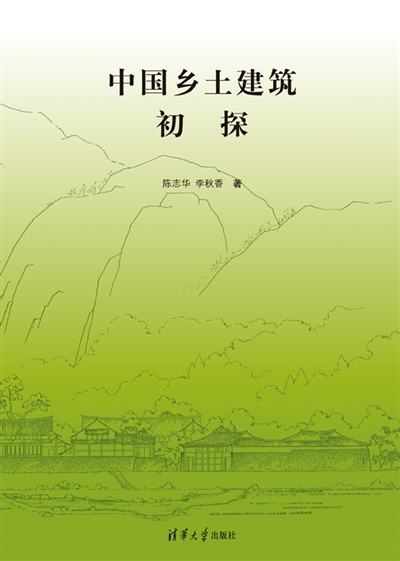
《中国乡土建筑初探》
作者:陈志华 李秋香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定价:185.00元

福建永定县某土楼破坏现状。 李玉祥 摄

福建永定圆楼破损后的修缮。 李玉祥 摄
陈志华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1929年9月2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系学习,1949年转入清华大学营建系,系主任梁思成。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当年留母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自1989年起,开始乡土建筑调查研究,曾出版《外国建筑史》《北窗杂记》《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外国古建筑二十讲》等。与李秋香合著新书《中国乡土建筑初探》日前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志华称因身体原因,这是他写作的最后一本书。
“这是一本远远没有完成的书。我不可能完成它,连起码的架子都搭不成。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可惜的是,我怕,我怕我们这个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已经永远没有人可以完成那本书了。”在《中国乡土建筑初探》这本书的后记里,陈志华这样写道。他担心“永远完不成”,是因为中国乡土建筑本身的拆毁速度看起来已经不太可能给后人留下书写和记录它们的机会了。
搞乡土调研被当美帝特务
从1989年到新叶村第一次进行乡土调查到如今,已经过去了23年,陈志华也从60岁到了83岁,20多年的时光投入,他却只肯说自己是对乡土建筑“初探”。“实际上‘初探’还说多了呢,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乡土建筑,破坏得实在太快。一个浙江省我们都还没搞明白呢,浙江70多个县,去了几个?没有人去,我们也来不及去。”
“暮年变法,学者之大忌。”但这件事在陈志华这里从未动摇过。因为对乡土建筑的热爱,他把干了大半辈子的学术工作扔掉,退休后就开始上山下乡,邀上了同校的年轻教师李秋香,而楼庆西也曾是这队伍中的一员。“我不能忍受千百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乡土建筑、蕴藏着那么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乡土建筑被当作废物,无情地大量拆除。”
最早的时候,他们连一张火车票也买不起。1989年浙江龙游有人请他们去测绘画图,想把村子里被破坏的建筑物搬家。从龙游出来以后,陈志华和李秋香到了千岛湖的建德,之后顺路去了新叶村。新叶村有个教书的老师,自己也喜欢建筑,叫叶同宽,曾经和陈志华讨论过一些问题,带着他们去老家参观。一到了新叶村他们就觉得村子里太漂亮了,有文昌阁、有大祠堂,房子也没怎么被破坏。
陈志华回到北京后就弄出了个研究提纲,想去当地调研,但是连调研的车票钱他们都没有,像样的相机也没有。陈志华走投无路,就又和叶同宽联系,写信说“我们给你写村子,你想办法弄弄车票。”叶同宽立即出了4张来回火车票的钱,陈志华立即让李秋香带着三个学生上了路。
楼庆西也曾表示过经费的困难是他们调研过程里最大的问题,最初台湾汉声愿意出他们的书,预付了一些稿费,他们就靠着预付的版税来支撑。卧铺坐不起,只能坐硬座,宾馆住不起,只能住在老乡家。他们一天的伙食费是五块七毛钱,粮食七毛钱一斤,剩下五块钱是菜费。
后来被陈志华一直拿来当古村落保护示范的诸葛村在最初调研时却十分危险,“我到诸葛村,当地官员以为我们是美帝的特务,认为我们很奇怪,怎么老是看破房子。”乡里来了好几次人和他们谈,问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还带着手铐和脚镣,想要把他们抓起来。“但村里的人和我们都是好朋友,有8个老头子,在警察来之前就知道了,跑来保护我们,我们才没被抓走。”
怎么能把房子造得像“兵营”一样?
虽然条件这么艰苦,但陈志华每次看见这些漂亮的村子高兴得不得了。香港有个电视台做节目,陈志华带他们去了一个村子,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下车,就手拉手拉了个圈,把陈志华围在中间,连跳带喊,他们喊“感谢陈老师把我们带到这么美的地方来!”
不过,这些都是调研头几年的事了,现在,这个村子已经都毁了,被毁的当然不仅是这个村子,“有什么办法呢?”陈志华这个问句也是无奈地感叹。
坐在从北京到宁波的飞机上,临下降的时候陈志华往外看,曾经美丽的村子都变成了“兵营”,山西、江西的好多村子也都一个样,北京也没逃掉。“前年春天的时候,北京说要竞选最美的村子,排第一号的村子竞选的时候就说‘我们的村子是最好的村子,因为全村的房子就只用一张图造的。’为什么用一张图就是最好的?这就是‘兵营’似的思想。”这个价值观让陈志华很不能理解,把房子造得和学生宿舍一样,但是学生的生活差不多,可农民生活却那么不同,养羊的、放牛的、喂猪的、种地的、教书的、做生意的,却都住在一样的房子里。
即便是对目前保护较好的诸葛村,陈志华也有一丝他的担忧。诸葛村20多年过去了,老房子基本上还和陈志华当年去的时候一个模样,新的房子村子里统一造,造在村子的背后。“我们去之前他们也在空地上盖过几个新房子,我们去了以后就停下来了。只要他们不拆老房子,这些新的饭馆之类的,我们看着也就不着急了。现在诸葛村卖门票发得很,一到假期公路上全是旅游车。”
重要的是得村子里得有一个过得硬的领导,“诸葛村的头头盯得住,后来的县委书记就当着我的面说,县里不干涉我们的工作。”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的领导快60岁了,换届之后会怎么样,陈志华不清楚。“换个干部会怎么样,我不知道,知道又怎么样?你说了谁听?一个大学老师而已……”
总得留几个年轻人替我
说了没有人听,却还得做下去,到现在资金也依然很紧张。现在学院里专职做乡土调研的人一共有6个,人手也不够,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你看我们系里除了我们搞乡土建筑的,谁没有车啊,一家还有两辆呢。像我们这样,打个出租车还有点拿不出钱来。”以前陈志华是全心全意穷,现在他也允许研究组的人偶尔接点赚钱的项目,“你知道为什么呢?”他停顿了一下自己回答“老婆都讨不上。”
“中国人穷,不是说少吃肉,而是受到侮辱,根本不把你当什么人。我10年不吃鸡也可以,但真的会受到侮辱,你得忍受这些东西。”“你们听说清华大学有这么两个人在搞乡土建筑研究,觉得还值得来访问访问,但你去建筑界看看,他们就说‘这两个人根本就是傻蛋,就是活该!’别以为出了几本书就怎么样,没有。”“建筑系毕业两三年就可以买车了,我们出一本书还要到处募捐。”“总共就这么几个人,这么点时间,工作量抢都来不及。”“我都84(虚岁)了,我还能怎么样?总得留几个年轻人,留一个替我啊!”
如果重视历史,我们会更文明
比起没有钱做调研和出书的事情来说,更让陈志华着急的还是,他们的调研速度远远赶不上乡土建筑被拆毁的速度。福建土楼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参观的人就多起来,当地立即把底层的住家房子拆掉,摆上饭桌供游客吃饭。(《中国乡土建筑初探》中收录了福建土楼破坏现状的照片,见右图。)
大部分的村子都搞改革,搞旅游,卖门票,门票一开始卖,老房子十个有八个就烂掉了。烂掉了人们也不在乎,觉得再造一个就好了,“本来那些老房子应该是历史文化教材,现在却全都是虚假的。全是假的还保护干什么呢?骗子孙的。”
意大利的古建筑是全世界保护最好的,陈志华有一年去意大利,一个小小的国家一年培养出3000个人来负责保护古建筑。旅游、门票这些都要有专人做出保护规划,他们会规定一个地方一天的游客不能超过多少人。日本的皇家花园一次只能进7、8个人,而且还得跟着导游走。“像我们的故宫,一年有8万人,这都发昏了,还自以为了不起呢。我们就要挤,挤不进去就要骂。”
故宫申遗的那一年,陈志华陪着英国费尔顿爵士在城墙上走,到了西北角往下面看,有个木匠拿了三根木头支起来,挂着水壶在烧开水。费尔顿爵士那时已经七八十岁,吓得跳起来,喊道“故宫里面怎么可以有火呢!”走到故宫后门的管理处,费尔顿看到墙上有棵长了20年的树,老头子又火了,他对管理员发火“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是世界遗产啊,不是你们中国人的,是全世界的,怎么可以长那么粗的树!”
后来又到天坛去,费尔顿发现自己坐的汽车打算直接开进去,他就急得直跺脚,“我们怎么可以坐着车进天坛呢!”陈志华赶紧骗他说:“因为你是专家,我们照顾你。”费尔顿立即说:“要是我坐着车进天坛,我还算什么专家!”
之后他们又去了敦煌,费尔顿看到墙上有潮气,就问这种水印和潮气都怎么处理。管理的人回答他们有仪器,费尔顿一看挂在墙正当中的仪器就又火了,“我问你,如果墙发生返潮的话,是从中央开始还是从墙角开始?!”
问陈志华遇见这些事是不是也和费尔顿一样生气,“我?我已经麻木了。别处这么干不稀奇,但敦煌这样过分了吧。敦煌啊!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面对那些有疑问到底为什么要搞乡土建筑保护的人,陈志华很想告诉他们,因为这是历史文化。文化不能当饭吃,也不都是很漂亮,如果没有人做,饭还可以照样吃,人还可以照样活,但是活得有文化和活得没文化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重视了历史,就会更文明一点,更善于思考,更知道好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么一大片土地蕴含着衣食住行,乡土建筑是这四大项的其中一项,如果将来弄得连个痕迹都没有了,有这样对待历史的吗?”
【记者手记】
陈志华的泪与苦笑
2008年3月的一个下午,在清华大学附近荷清苑小区陈志华的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背对着窗户,我们起初是聊他出的一本新书,之后就谈到了古村落的消亡,说着说着他哭了,用手抹了一把眼泪,这对他来讲是个沉重伤心的话题,尽管彼时他身后夕阳西下是幅美景。4、5年后,再次见面依然是在同一个空间,依然是一个下午,采访结束后的两个月,他要去住院。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回答:“我现在就在住院。”对他来说,只要没有在做乡土建筑调研工作的日子里,就和住院没有区别,尽管他已经83岁。我们的采访依然避不开几年前让他落泪的话题,讲起这些他有一肚子的话,却不再有泪,我听到最多的是他的苦笑。问他还难过吗?他回答“麻木了。”
我想,我忘不了几年前他的泪,我更忘不了如今他的“笑”。
【陈志华说】
保护古建比登月还要新鲜
我母亲是纺织能手,但不识字,甚至没有名字,只叫“大丫头”。我幼年时候,母亲告诉我,我是我父亲在“湾”(水塘)边一锄头挖出来的。但在我出疹子的那些日子里,她在床边给我唱了许多民歌,都那么有趣,那么好听,到现在我还能背出几首。整个八年的抗日战争,我都在深山老林里的流亡学校里读书,高小和中学。衣食不周的饱学老师教养着我们,勤劳慈善的山村大婶怜爱着我们,我一生最记得牢的一句白话诗是艾青写的:“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把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土地上,有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我忘不了他们。
为了这个爱,我把干了大半辈子的学术工作都扔掉了,一退休,当年就决心上山下乡,邀上年富力强也曾在农村生活过的李秋香老师去调查祖国的乡土建筑。一度还有楼庆西老师合作。“暮年变法,学者之大忌”,我却没有半点留恋和动摇。我不能忍受千百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乡土建筑、蕴藏着那么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乡土建筑被当作废物,无情地大量拆除。有些竟是整村整村地拆除。我们当然有能力造出更舒适、更安全、更方便的崭新的农舍来,但我们,我们任何人,造不出几千年的历史、造不出古老的文明、造不出先人们的奉献。忘记祖先,不等于进步;进步不能以鄙薄祖先为标识。哪一个人,敢忘记老祖母脸上的一块疮疤,更何况那其实是一粒美人痣!祖先们发明了钻木取火,那智慧远远大于你使用电脑。你开着最新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跑,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作的贡献却远远不及祖先们驯服了一匹野马。我们现在当然要电脑,要新式汽车,要用功夫去创造更先进得多的东西,但我们要记住祖先们是怎样含辛茹苦、坚持创造和进步的。我们要懂得感谢。我们还要明白,一切伟大的发明创造,依靠的都是从钻木取火和驯服野马之类的成功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好在世界没有在空前的进步大潮中失去理性、鄙薄过去,相反,进步提醒了人们尊重过去,是过去的人创造了今天人们享受着的进步,于是,几乎全世界都掀起了汹涌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浪潮。保护古建筑和古建筑群体成了世界性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按时代说,比人类登月还要更新鲜。它是向前探索、向前开拓的回应。它一点也不拖累前进的脚步,它的追求是保证一切向前的运动只会使人类的文明更丰富、更有活力、更深入每个人的胸怀,而不是逼迫人们忘记历史,失去对文明创造者的尊敬之忱、感激之心。这样的思想感情,会是人类进步的障碍吗?
……
我们盼望同道朋友们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摄影和写作的,最好还有奋身投入乡土建筑的保护工作中来的。请朋友们原谅,我用了“奋身”这个词。我敢告诉朋友们,退休之后,也便是我们乡土建筑调研工作开始之后,除了住过几次医院,二十二年来,我天天都在工作,包括现在这个除夕夜,窗外正闪烁着烟火,炸响着鞭炮。当然,我还是要为我们工作的粗疏和知识的欠缺向朋友们道歉!
——录自《中国乡土建筑初探》作者后记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见习记者 江楠
人物摄影/实习生 王政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