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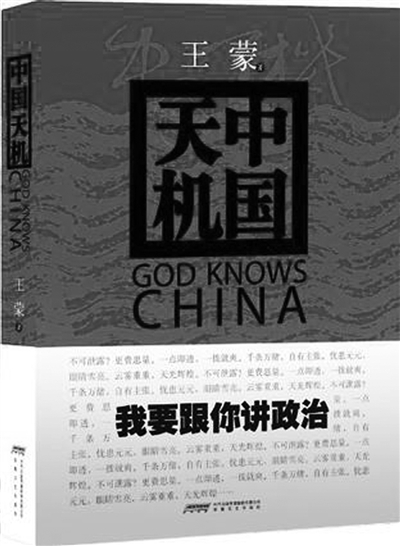
《中国天机》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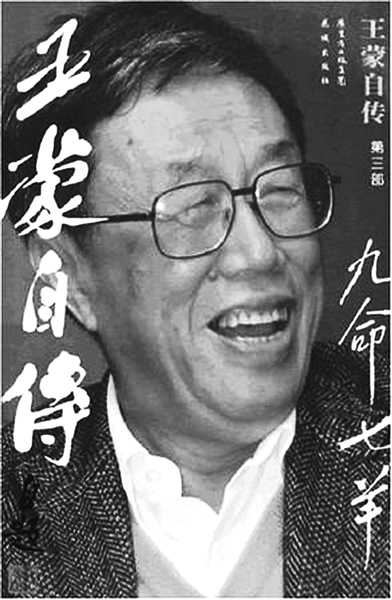
《九命七羊》
花城出版社
2008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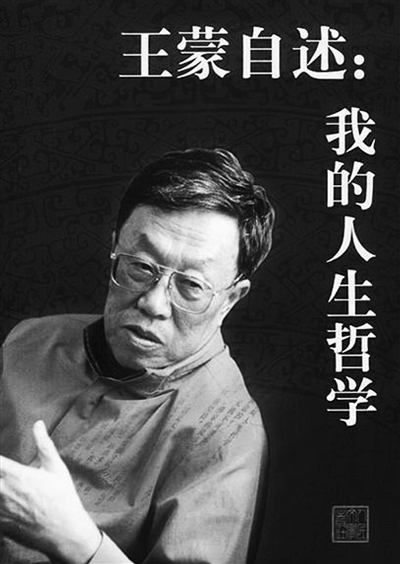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1月
(上接B02版)
谈政治态度 “对一切我都不抱幻想”
新京报:感觉书里,你特别服膺中国革命。这种观点,是因为你自己从事革命,所以有强烈的感情吗?
王蒙:当然,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不相干的事,我可以说从少年时代、童年时代,就扑在这个上头了,而且我一回忆起来,完全能够重新回到那个开始接受革命圣火的时候,那种崇高感,那种献身的感觉,那种服膺的感觉,五体投地的感觉,就是世界上有这样的理论,有这么伟大的理论,有这么伟大的实践。
当然,事后,很显然你的设想和事实不可能完全一致,除非你要求你的设想就是百分之百兑现,那你就会非常失望。如果你知道你的设想不可能百分之百兑现,你反倒会乐观一些。
张承志有个小说里头他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我记得的并不完全是原文了,他说世界上只有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有权乐观,我觉得他这个话非常好。我就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对一切我都不抱幻想。这样的话,我反倒乐观,知道它会出现一些问题,也会有一些我们不希望出现的问题出现,这个不足为奇。
新京报:早年你写过《青春万岁》,现在回忆起来是不是也有青春无悔之意?
王蒙:当然有这个意思,而且我觉得好像《青春万岁》,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并不是我最重要的小说。但这个小说毕竟是一个记录,而且是唯一的记录。
你不能够忘掉这一点,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王蒙,那时候才十四五岁,还包括现在人们都非常尊敬的一些大的知识分子,解放以后都是最热情投入革命中的,比如说我知道的语言学家罗常培,那种热情,语言学家吕叔湘,哲学家冯友兰等等。
新京报:你体现出的政治态度,是要戒急戒躁,如果前面走得太快会有问题,如果没想明白,宁可慢一点也行。
王蒙:中国发生这些悲哀,大部分是由于急躁所造成的。包括像大跃进、全民公社化等等。但是,我同样非常痛切地陈述目前的这些忧患。而且我说的那些事情在我之前,包括那些抱极端批评、否定态度的人,他们并没有说过这些事情。
我想写这些革命经历,与其说是辩护,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我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因为如果你对历史的看法,是现在网上某些人的看法的话,那中国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土改不可能发生,参军不可能发生,《白毛女》就不可能演。
你必须理解这个历史是怎么发生的,至于说这个历史你喜欢不喜欢历史成为这个样,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与其去设计历史的可能性,和寻找这个历史的责任,不如我们设计当今的可能性,当今的责任,当今能够改善的可能。如果你一边痛骂着历史,一边你又对今天不负任何的责任,我觉得那样的话,中国就会只能变得更坏。
谈处世哲学 “我并不否认我的中庸”
这套丛书共包括《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第一部)》,《大块文章(第二部)》,《九命七羊(第三部)》三本,第三本主要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王蒙的一些经历,其中包括推荐诺贝尔文学奖人选和推荐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等争议性的事件。王蒙不像平民作家那么单一,他身上折射着太复杂的因素。
新京报:有评论说你是“国家的仆人”,感觉很多时候,你小心翼翼。这种处世思想是怎么形成的?
王蒙:中国因为缺少多元制衡传统,中国的平衡表现在时间纵轴上,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此中国在政治道德上最强调的是中庸,(勿为己甚),留有余地,过犹不及。在中国,尤其你,因为国外也没关系,多偏激的理论都没有关系,因为它有这么偏激的,它还有那么偏激的。
所以你如果说我是一个中庸者,我并不否认,这是中国国情和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我为什么要写《中国天机》这本书,我就是与其让一些人没完没了在那瞎猜,瞎理解,还不如我干脆给你公示一下我到底对很多事情,恰恰是这些最尖锐的大问题上,我是怎么想的。
第二点,我不赞成那么急于做价值判断。我更多地要说我所感觉到的真实发生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比如说搞运动,一搞运动,一开头大家都想不通,三弄两弄就弄成真的了,我在小说里也写过这些场面,这个书里我写得更透彻,更清楚。
我觉得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把价值判断放在前头,而不考虑认知判断。鲁迅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人们看一个匾,都还没看清楚什么字呢,但是两边已经打起来了,一部书法的匾,他认为比如说这个字写得好,那边认为这个字写得不好,双方的意见非常不一致。但是那匾上到底写的什么还都不知道,他原来想的,因为眼睛都近视……鲁迅专门讲过这个。
谈批评与争议 “‘妖精’是个好话”
王蒙关于人生修为的集成之作。他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传奇体验,剖析人生的各个环节,讲述人之为人、人之为事的种种道理。是一个老作家的回首,和对自己几起几伏、大起大落一生的评价。
新京报:对你的批评中,有人说你像个“泥鳅”,前两年还有人说王蒙是“妖精”,你当时也认了。是什么原因让你能炼成今天这样?
王蒙:这说明他一点都不了解王蒙,因为他太浅了,如果要是泥鳅的话,他写不出这种书来,这样不回避自己的观点,尽管他很慎重,措词上,但是毕竟他把该说的话说了,这是不可能的。
“妖精”是个好话,说他成了精了。比如说这次关于这书,有一个说法,说是能够掌握这样一个分寸,能够拿捏这么一个火候,除王蒙外,休做第二人想,他这个用词还挺逗,不像现在年轻人用词,不是说没有第二个人了,它叫休做第二人想,他把这个想动词放在最后来了,这个人读过点老书,40岁以上。
我看了以后当然很得意,不成了精能够做到这一步吗?我在银川书博会上还引用,我说人民日报张社长曾经对我讲过,他说他到人民日报去赴任的时候,提出三句话,要“敢说话、说新话、会说话”。我说这个我很赞成的,因为它是人民日报,它不可能像网上一样,像博客一样,像微博一样。所以,是这么一个意思。
新京报:在文学界的各种论争中,你曾经保护过作家王朔,你说应该有不同的文学作品。这种多元的思维,也是基于自身的经验和教训形成的吗?
王蒙: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咱们国家写小说的人,喜欢文学的人,我们最喜欢强调这个话,官方也强调,有时候本人也强调,就是“深入生活,从生活出发”。所以,我就用我的生活,我对生活的感悟,对生活的认知,对生活的挂牵,对生活的坚持,来衡量我们的社会,来衡量这些官方的理论,也来衡量这些小哥们的咋咋呼呼的呐喊,也包括非常美好的声音,所以我说我要做的就是“用生活来解说文学和政治”,这跟我这一个人是统一的。
还有人批评说写这个书是转向的,我说我哪转向了,本来这就是写我的生活。
B02-B03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弘










